
- 替嫁三年,他把我当狗养苏薇薇陈景深完整版免费阅读_苏薇薇陈景深精彩小说
- 分类: 其它小说
- 作者:s文熙
- 更新:2025-07-30 06:34:00
《替嫁三年,他把我当狗养苏薇薇陈景深完整版免费阅读_苏薇薇陈景深精彩小说》精彩片段
“林小姐,你妹妹失血过多,急需一种非常罕见的免疫蛋白,我们医院没有库存。
”医生的话像一把钝刀子,在我脑子里来回地割。我看着抢救室亮起的红灯,
整个世界都在天旋地转。就在今天早上,我的妹妹林小月,作为今年的高考状元,
还在电视上接受采访。她扎着马尾,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对着镜头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赚钱养我姐姐,带她环游世界。”可现在,她躺在里面,
生死未卜。咬她的是一条比特犬,主人是我结婚三年的丈夫,陈景深养在外面的情人,
苏薇薇。“免疫蛋白……”我喃喃自语,像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陈景深有,
他一定有办法。我颤抖着手,拨通了他的电话。电话那头很吵,
是震耳欲聋的音乐和男男女女的嬉笑声。“喂?”陈景深的声音带着一丝不耐烦。“景深,
是我。”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小月……小月被狗咬了,在医院抢救,急需免疫蛋白,
你……”“林星辰,你又想耍什么花样?”他冷笑着打断我,“为了让我回家,
连你妹妹都拿来当借口?你就这么贱?”“不是的!是真的!她在市中心医院,
医生说再没有免疫蛋白她就……”“嘟……嘟……嘟……”电话被他挂断了。
我像被抽干了所有力气,瘫坐在医院冰冷的长椅上。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攥住,
疼得我无法呼吸。不行,我不能放弃。小月还在等我。我冲出医院,拦了辆出租车,
报出那个我只去过一次的地址——陈景深的私人会所。推开包厢门的瞬间,
奢靡的酒气和香水味扑面而来。陈景深就坐在沙发正中央,苏薇薇像条蛇一样缠在他身上,
正娇笑着喂他喝酒。看到我,陈景深眉头一皱,眼神里的厌恶毫不掩饰。
苏薇薇则挑衅地看了我一眼,红唇勾起。我顾不上那么多了。“噗通”一声,
我跪在了他面前。包厢里瞬间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像看戏一样看着我。“陈景深,我求你,
救救小月,她快死了!”我仰着头,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我什么都不要了,
只要你救她,我马上签字离婚,净身出户,从你眼前消失!”陈景深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眼神冷得像冰。“林星辰,你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他身边的苏薇薇发出了一声轻笑,
嗲声嗲气地说:“景深,姐姐这是怎么了?是不是误会了什么?我的小可爱平时很乖的,
怎么会咬人呢?”“小可爱?”我死死地盯着她,“你的狗把人咬得快死了,
你管它叫小可爱?”“哎呀,”苏薇薇夸张地捂住嘴,“姐姐你别吓我,我胆子小。
”陈景深终于不耐烦了,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黑卡,扔在我脸上。“拿着钱,滚。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卡片冰冷的棱角划过我的脸颊,像一记耳光。
他搂着笑得花枝乱颤的苏薇薇,头也不回地从我身边走过。那一刻,
世界的声音好像都消失了。口袋里的手机疯狂震动,我木然地接起。是医院打来的。
“林小姐,请节哀。病人……抢救无效,于三分钟前确认死亡。”……小月的葬礼很简单。
来的人不多,只有我和婆婆顾婉。陈景深没来。我穿着一身黑衣,
麻木地站在小月的黑白遗像前。照片上的她,笑得还是那么灿烂。婆婆叹了口气,
拍了拍我的肩膀:“星辰,景深他……被那个狐狸精迷昏了头,你别往心里去。”我转过头,
看着这个待我一直不算差的女人,声音平静得没有一丝波澜。“妈,我要和陈景深离婚。
”顾婉愣住了。我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是苏薇薇昨天发给我的。照片里,
她戴着一条钻石项链,正是我生日时陈景深送我的那条,配文是:“谢谢姐姐的礼物,
景深说,还是我戴着更好看。”顾婉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这个不知廉耻的女人!
”我没说话,只是当着她的面,拨通了陈景深的电话,按了免提。响了两声,电话被接起,
传来的却是一个娇媚的女声。“喂?找景深吗?不好意思哦,他现在在洗澡,不方便接电话。
”是苏薇薇。我依旧沉默着。电话那头的苏薇薇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轻笑了一声,
语气里的恶意像是毒液,透过听筒蔓延开来。“哦,原来是林大善人啊。怎么,
给你妹妹收完尸了?骨灰盒在哪呢?要不你送过来,给我磕三个响头,我说不定一高兴,
就让你把她带回去了。”“啪嗒。”是婆婆手里的佛珠串,断了。珠子散落一地,
发出清脆又绝望的声响。十几颗温润的珠子,砸在冰冷的地砖上,四散滚开,
像是我们这个家,分崩离析。顾婉的身体晃了晃,脸色灰败。她看着我,嘴唇哆嗦着,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眼里的愧疚几乎要满溢出来。我平静地挂断电话,将手机放回口袋。
“星辰,妈对不起你……”顾婉的声音带着哭腔,“是我……是我没教好他,
让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我摇了摇头,看着她一夜之间仿佛老了十岁的脸,
心里竟没有太多波澜。“妈,不怪你。”我的声音很轻,“当初是我自己选的。
奶奶要做心脏搭桥,小月要上最好的高中,没有顾家,我们姐妹俩撑不下去。
”这是我和陈景深婚姻的真相。十五岁那年,同为地质专家的父母在一次山区救援中牺牲,
被追授烈士。荣誉和抚恤金,远不够填补奶奶的医药费和我和妹妹的生活。走投无路时,
顾家找到了我。他们需要一个八字相合的儿媳妇,来冲一冲陈景深身上的“煞气”。
一纸契约,换我奶奶十年安康,换我妹妹前程无忧。我签了。顾婉的眼泪掉得更凶了,
她从随身的包里,颤抖着摸出一个已经有些泛黄的牛皮纸信封。“这个……你拿着。
”她把信封塞到我手里,“三年前,A大李教授给你的留学推荐信。本来早就该给你的,
是景深……是他给扣下了。”我低下头,看着信封上熟悉的字迹。李教授曾说,
我是他教过最有天赋的学生,只要我愿意,他可以保我到国外最好的设计学院深造。原来,
我不是没有机会。是陈景深,亲手折断了我的翅膀。“他说什么……不想让你走,
说你走了谁来照顾他。”顾婉泣不成声,“都是借口!他就是想把你拴在家里,这个畜生!
”我捏着那封信,指节泛白。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些画面。也是三年前,我们刚结婚不久。
他有一次喝多了,靠在沙发上,拉着我的手,眼睛里有我看不懂的迷茫。“林星辰,
你好像什么都会。你教教我,怎么去爱一个人。”那时候,我真的以为,他那颗石头做的心,
是能被我捂热的。可后来呢?后来,他开始彻夜不归。我等他到深夜,给他端去醒酒汤,
他一把挥开,滚烫的汤洒了我一手。“滚开,别碰我,跟个老妈子一样烦人。”再后来,
顾婉在饭桌上催我们生孩子,他当着所有人的面,用筷子指着我,笑得轻蔑。
“她不就是个生育工具吗?着什么急。”最可笑的是我二十五岁生日那天。我花了一下午,
做了满满一桌他喜欢吃的菜,傻傻地等他回来。等到最后,他回来了,却不是一个人。
他带着苏薇薇,还有一群狐朋狗友,把家里搞得乌烟瘴气。苏薇薇端着一杯红酒,
摇曳生姿地走到我面前,脚下一崴,整杯酒都泼在了我新买的白裙子上。“哎呀,姐姐,
对不起啊,我不是故意的。”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陈景深就走了过来。我以为他会为我出头。
结果,他端起另一杯红酒,从我头顶,浇了下去。冰凉的液体顺着我的头发流进眼睛里,
又涩又痛。我听见他在我耳边说:“穿得人模狗样的给谁看?不就是想要钱吗?
”一张黑卡被甩在我脸上,像一片冰冷的雪花。“拿着,滚去换身干净的衣服,
别在这儿碍眼。”……思绪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我打开门,
外面站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请问是林星辰女士吗?”其中一个警察出示了证件,
“关于林小月女士被恶犬所伤一案,我们需要您配合做一份笔录。”我点了点头,
正要请他们进来。一辆黑色的宾利悄无声息地滑到门口,车门打开,
陈景深一身戾气地冲了下来。他一眼就看到了门口的警察,随即目光像刀子一样射向我。
他几步冲上台阶,一把将我拽到身后,对着警察挤出一个僵硬的笑。“警察同志,误会,
都是误会。家里的事,我们自己处理就好。”说完,他压低声音,
在我耳边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音量说。“林星辰,你玩真的?敢报警?
”他的手像铁钳一样攥着我的胳膊,力气大得像是要把我的骨头捏碎。“我警告过你,
苏薇薇要是受了半点委屈,我要你妹妹……”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他终于看清了我。
警察的话还没说完,陈景深已经处理妥当。他对着两位警察,
脸上挂着那种我最熟悉的、属于陈家大少爷的假笑。“警察同志,辛苦你们跑一趟。
一点家事,我太太不懂事,闹了点小脾气,都是误会。”他三言两语就把人打发走了,
警察大概也觉得清官难断家务事,嘱咐了几句便离开了。门一关上,
那张伪善的面具瞬间撕裂。“林星辰,你长本事了。”他一步步逼近,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学会报警威胁我了?”我的胳膊被他抓住,力道大得像是要生生折断。他拖着我,
就像拖着一件不想要的垃圾,径直往门外那辆黑得发亮的宾利走去。我没有挣扎,
甚至没有说话。有什么好说的?跟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解释就是浪费口水。
他把我甩进副驾驶,车门“砰”地一声关上,震得我耳膜发疼。他倾身过来,
车内的空间瞬间变得狭窄逼仄,全是他的气息,混杂着另一种女人的香水味。
“为了那个苏薇薇,你连警察都敢叫?”他捏住我的下巴,强迫我看着他,“我警告过你,
别动她。她要是受了半点委气,我就让你妹妹……”他顿住了,似乎在寻找最恶毒的词汇。
“……千倍万倍地还回来。”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可笑。还?拿什么还?
小月已经把命都还给你那宝贝情人的“小可爱”了。我的沉默似乎彻底激怒了他。
他眼里的怒火几乎要喷涌而出,大概是觉得我在用这种方式跟他对抗。“不说话?装死?
”他冷笑,“林星辰,你费尽心机不就是想让我碰你吗?结婚三年,
你在床上不也跟死鱼一样?怎么,现在换策略了?”他的脸越靠越近,
那张曾经让我心动的嘴唇,此刻却只想让我作呕。“好啊,我满足你。”他说着,
就真的吻了下来。那一瞬间,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用尽全身的力气将他狠狠推开。
他的头撞在车窗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车里死一般地寂静。他好像愣住了,
不敢相信我敢推他。我看着他,胸口剧烈地起伏着,胃里翻江倒海。“啪!
”一个清脆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我脸上。火辣辣的疼,从左边脸颊迅速蔓延开来。
我的头被打得偏向一边,耳朵里嗡嗡作响。“林星辰,你他妈的给脸不要脸!”他咒骂着,
摔上车门,引擎发出一声咆哮,车子绝尘而去。我被独自留在了路边,
像一个被丢弃的破旧玩偶。夜风吹过,脸上的疼痛愈发清晰。我慢慢地抬起手,
摸了摸发烫的脸颊。不疼。真的,一点都不疼。心都死了,身上这点伤,又算得了什么。
我站直了身体,整理了一下被他扯乱的衣服,一步一步,走得异常平稳。第二天,
我去了民政局,又去了公安局。死亡证明的纸张很薄,拿在手里却重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把刀,在我心上反复切割。林小月,女,十八岁。
死亡原因:失血性休克。我拿着那张纸,在电脑前坐了很久。然后,我用自己的社交账号,
发布了一则讣告。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悲痛欲绝的哭诉。
只有几行冷静到近乎残忍的文字。“吾妹林小月,于公历二零二三年十月二十六日,
因意外离世,年十八。兹定于下周一上午十时,于西山殡仪馆举行告别仪式。特此讣告。
——姐,林星辰。”做完这一切,我关掉电脑,拉上了窗帘。讣告发出去的第二天,
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巨响震得墙上的灰都簌簌往下掉。陈景深冲了进来,
手里捏着我的手机,屏幕上正是我发的那条讣告。他双眼通红,
像是刚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周身都裹挟着一股暴戾。“林星辰!
”他把手机狠狠摔在地上,屏幕瞬间四分五裂。“你他妈有种!为了钱,连自己妹妹都敢咒?
”他身后,跟着一脸泫然欲泣的苏薇薇,她怯生生地躲在陈景深背后,只露出一双眼睛,
像是在看什么脏东西一样看着我。我没理他,只是低头看着地上散落的白色纸钱。
那是婆婆顾婉早上送来的,她说按规矩,头七之前,家里不能断了香火和纸钱。
陈景深见我不说话,怒火更盛。他从怀里掏出一沓厚厚的现金,劈头盖脸地朝我砸过来。
红色的钞票像雪花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有的落在我脚边,有的飘在小月的遗像上,有的,
甚至落进了奶奶的骨灰盒旁边的香炉里。“够不够?”他咬着牙,“不够我再加!
让你妹妹死一次,开个价!”我慢慢地蹲下身,一张一张地,把那些沾了香灰的钱捡起来。
动作很慢,很轻,仿佛那不是钱,而是一片片破碎的羽毛。我的平静,
似乎比歇斯底里的哭喊更能激怒他。他的手机在这时响了。是苏薇薇的。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立刻接了起来,开了免提,声音娇滴滴的,带着哭腔:“喂?
警察先生……我,我真的不知道……那狗平时很乖的……”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我听不清。
只看到苏薇薇的脸一瞬间变得惨白,她抓着陈景深的手臂,抖得像秋风里的落叶。
同类推荐
 退婚PUA白眼狼,禁欲军官他真香(沈俊彦陆擎川)好看的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推荐退婚PUA白眼狼,禁欲军官他真香沈俊彦陆擎川
退婚PUA白眼狼,禁欲军官他真香(沈俊彦陆擎川)好看的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推荐退婚PUA白眼狼,禁欲军官他真香沈俊彦陆擎川
慕容书生
 苏芮林海(我们成了祖先)全章节在线阅读_(我们成了祖先)完结版免费阅读
苏芮林海(我们成了祖先)全章节在线阅读_(我们成了祖先)完结版免费阅读
雄鸡凤凰
 玄学大师穿成霸总里的扫地僧宫斗宅斗祝昶新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玄学大师穿成霸总里的扫地僧(宫斗宅斗祝昶)
玄学大师穿成霸总里的扫地僧宫斗宅斗祝昶新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玄学大师穿成霸总里的扫地僧(宫斗宅斗祝昶)
余浅生
 血嫁红绣鞋宋言林婉清热门小说阅读_免费完结小说血嫁红绣鞋宋言林婉清
血嫁红绣鞋宋言林婉清热门小说阅读_免费完结小说血嫁红绣鞋宋言林婉清
邪恶小军师
 全世界都比不过我的小竹马(江屿林辰)全章节在线阅读_江屿林辰全章节在线阅读
全世界都比不过我的小竹马(江屿林辰)全章节在线阅读_江屿林辰全章节在线阅读
陌上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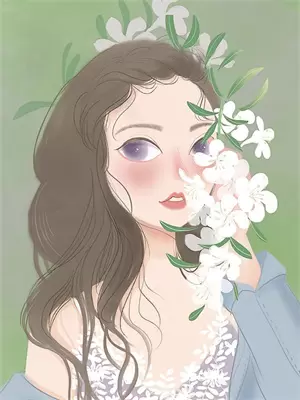 春腾生长时冰冷林小满全文阅读免费全集_最新全本小说春腾生长时(冰冷林小满)
春腾生长时冰冷林小满全文阅读免费全集_最新全本小说春腾生长时(冰冷林小满)
泔水的硕妃
 教育公平(保送内定后我退学让全市震动了)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保送内定后我退学让全市震动了完整版免费在线阅读
教育公平(保送内定后我退学让全市震动了)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保送内定后我退学让全市震动了完整版免费在线阅读
快乐的小皮皮
 被PPT砸死后我成了规则制定者(冰冷怨念)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推荐被PPT砸死后我成了规则制定者冰冷怨念
被PPT砸死后我成了规则制定者(冰冷怨念)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推荐被PPT砸死后我成了规则制定者冰冷怨念
第根号三支羽毛
 恐游大boss是我网恋前男友游乐幽幽完结好看小说_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恐游大boss是我网恋前男友(游乐幽幽)
恐游大boss是我网恋前男友游乐幽幽完结好看小说_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恐游大boss是我网恋前男友(游乐幽幽)
m糖炒冰栗子
 小三将爸爸当活靶子后,我杀疯了(宋墨晴顾翰章)在哪看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小三将爸爸当活靶子后,我杀疯了(宋墨晴顾翰章)
小三将爸爸当活靶子后,我杀疯了(宋墨晴顾翰章)在哪看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小三将爸爸当活靶子后,我杀疯了(宋墨晴顾翰章)
浮清鱼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