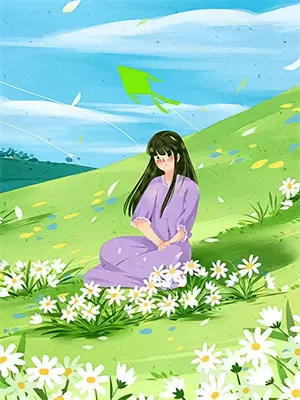- 余套子的传奇故事(兰博正义)最新完结小说推荐_热门小说排行榜余套子的传奇故事兰博正义
- 分类: 其它小说
- 作者:正义的兰博
- 更新:2025-07-30 06:21:51
《余套子的传奇故事(兰博正义)最新完结小说推荐_热门小说排行榜余套子的传奇故事兰博正义》精彩片段
在河南孟津县的老城村里,烈日炙烤着龟裂的土地,日子漫长而艰辛,
村里住着一个名叫余套子的男孩。他的真名具体叫什么,连我的父辈们都说不清楚,
只知道他的外号叫“套子”。这个外号的来由是,他家里太穷,没有衣服穿,
冬天经常穿一个“烂棉花套子”,且这个套子,还是他母亲在他姨妈家,
寻他一个表哥穿剩下的。寻来的时候,那套子本来就是烂的,他也不讲究,光膀子直接套上,
不冷就行。所以,我听父辈们说,他原来的外号,是叫“烂套子”,但叫着叫着时间久了,
就简化成了“套子”。“烂套子”下的童年余套子,一九五五年,
出生在河南省孟津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家里姊妹五个,他排行老二,是唯一的男孩,
有一个大姐和三个妹妹。他从八岁起,就跟随父母一起下地干活,
日子与村里其他孩子没什么两样,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周而复始。然而,
余套子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对文字的热爱接近于痴迷。那个年代,物资极其匮乏,
余套子家穷得买不起书,上学对他来说更是遥不可及的梦。所以,
他小学一年级没读完就辍学了,但即便如此,他依然保持着对文字的热情。余套子没练过字,
但从小字就写得极好,语言表达能力也很强。
这一点也得到他小学班主任语文老师的高度赞赏。他退学那会儿,
班主任老师还专门找到他爹余强,试图让他继续留下念书,
可是面对眼前拮据的家庭条件,余强还是摇摇头,坚持让他退学。
教室里的机智与惩罚还记得上学那会儿,村长家的小儿子刘喜旺和余套子是同班同学。
刘喜旺有一天下午不想上课,于是中午放学后便找到余套子商量:“套子,套子,
给你商量个事儿。”余套子愣了一下:“什么事儿?”“套子,今天下午我实在不想上课,
我想跟表哥一起去后街桥下河里摸鱼,都约好了。你能不能在黑板上写几个字,
下午放假半天”,刘喜旺笑眯眯着说着。接着又说:“你要答应我,我就分你一点黄豆,
再给你切五片咸菜。”余套子顿了顿:“黄豆和咸菜先分给我一点,我再考虑。”“行行行,
没问题,现在就给你分”,刘喜旺一听余套子答应了,乐坏了。就这样,
余套子得到了一小把用报纸卷着的黄豆,还有五片咸菜。他高兴坏了,
心想:这两样东西带回去给爹吃,爹一定很高兴。刘喜旺很守信用,余套子也拿到了东西。
两人快马加鞭的返回教室,余套子拿起粉笔在黑板上,
模仿起语文老师的字迹:下午放假半天。到了下午上学后,学生们进教室一看,信以为真,
真的纷纷回家了。等到班主任进教室时,已经空无一人。当他还纳闷时,
扭头一看黑板上的几个大字:天哪,坏了!这确实像我的字,而且是特别的像,
我什么时候写过这几个字呢?难道是我中午午睡梦游了?最后调查了一圈,才查出来真相,
门口的看门老头看见了刘喜旺和余套子中午进教室了。黄豆和咸菜,他确实带回去了,
他爹当时也确实高兴了,也吃进肚子了。但即便如此,余套子还是挨了一顿打。
田埂上的书法梦乍一看,他与村里其他孩子并无两样——皮肤晒得黝黑,双臂瘦得像芦苇,
衣服上满是补丁,流着鼻涕也不擦。与同龄孩子追打、嬉戏不同,余套子最喜欢的,
却是趁大人们休息时,在田埂边的黄土地上,用树枝写字。尤其是收庄稼时,别人忙着赶场,
他却趁机捡拾掉落的报纸、包装纸、药箱封面上的印刷字;拾来便如获至宝,
认认真真地抠字、一笔一划地临摹。遇到不认识的字,他也没人可问,
因为村里识字的老人屈指可数,年轻人又都忙着下地干活,没时间搭理他。
他只能把这些生字记在心里,留待下次机会。有时在路上遇到熟人,他嘴甜,
赶紧喊声“叔叔”“伯伯”,然后捡根树枝在地上写出那个字,问人家怎么读。
如果对方认识,随口一说,他就高兴得像得了宝贝;可有时他写的字对方也看不懂,
因为他本来写的就是一个错别字,他只能继续把这字揣在心里,
回家翻江倒海去寻找这个生字怎么写。大队里无酬的“文秘”天赋这种东西确实是存在的,
余套子的字写得漂亮,笔锋遒劲,哪怕是在泥地上练出来的。
他的书法和表达能力在村里小有名气,乡亲们都说:“这余家小子,不太一样。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毕竟在那个年代,种庄稼得粮食才是正事。
余套子的父亲余强是个地道的庄稼汉,多年劳作让他性格变得坚硬,
观念里只有生存这个道理。据说,余强的父亲就是在1942年河南大逃荒时,
饿死在路上的。所以,在他看来,读书写字远不如一袋粮食来得实在,“百无一用是书生,
”他常抱怨,觉得余套子痴迷文字是在浪费时间。家里五个孩子,余套子是唯一的男丁,
他爹希望他能多干活,撑起这个家。余套子的母亲心肠稍软,
对儿子的爱好既不反对也不支持,但在那个年代,农村女人在家里几乎没有话语权。
余套子只能偷偷摸摸地学字,藏起他的纸片,在月光下练字,锄地时默背生字。十年过去,
余套子几乎认全了所有常用字,除非是特别生僻的字,其它他都能读会写。
他的这个长处在村里逐渐传开,村里大队需要写大字报或广播稿时,都会找他帮忙。
没有报酬,顶多是大队长偶尔赏他一个鸡蛋,但余套子乐在其中。每一次动笔,
都是他与文字的对话,哪怕得瞒着父亲。包办婚姻与失落岁月余套子十八岁那年,悲剧降临。
母亲因肺痨病逝,家中本就拮据的生活雪上加霜。临终前,
母亲叮嘱余强赶紧给套子找个媳妇,照顾这个家。余强年事也已高,孤身一人,
便听从了妻子的遗愿。那个年代,还流行着包办婚姻。
余强平时与村头磨面的王麻子比较熟悉,两个人也走的比较近。
他与村头磨面的王麻子一拍即合,按照当时的习俗,
定下了余套子与王麻子二女儿王俊丽的婚事。王俊丽读过几年书,能识些字,
平时帮她爹记账。余套子见她识字,心里颇为满意,以为他爹办了一件好事,自己找对了人。
但婚后,他发现王俊丽性子泼辣,蛮横不讲理,啥事稍有不顺她的心,就会指着他一通骂。
余套子虽然也算没上过学,但毕竟还上过半年多小学,再加上平时爱自学,
也算是一个“文化人”。他不愿争吵,遇到不顺心的事,他就到院子里拿树枝在地上写字,
东一笔西一划,直到写满整个院子。这日子,虽然不算太顺,但忍忍也能过。然而,
谁都不知道的是,更大的悲剧接踵而至——婚后多年,王俊丽的肚子始终没有动静。
在那个重视传宗接代的年代,余套子作为家中独子,这成了全家人的心病。两人四处求医,
喝了无数中药,甚至请来村里的“半仙儿”做法事,可五年过去,依旧毫无结果。
王俊丽不反思自己,却一口咬定是余套子的“种子”不行。她的指责如刀,刺得余套子心痛,
但他只是默默忍受,继续拿树枝在泥地上写来写去。五年后,王俊丽依然没有生出孩子。
王麻子护女心切,找到余强大闹一场,指责余家隐瞒了余套子的“毛病”,害了他家女儿,
他要求王俊丽与余套子马上离婚,并赔偿他家五袋粮食。无奈下,老实的余强只能勉强答应。
王俊丽与余套子离婚后,王麻子继续撮合,带她改嫁给前街的一个瓦匠。但讽刺的是,
王俊丽改嫁后,肚子依然没有动静,村里的流言开始转向。家变与绝望远行有时候,
这人要是倒霉,真的是喝口凉水都能噎着。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村里谁家离婚,
那就是天大的事情,自己丢人现眼,还会被全村的人指指点点。就这样,
老余家离婚的消息一直没有平息,舆论的压力让余家一天比一天强,
直到接着一起悲剧再次降临到老余家。余强是一个老实的庄稼人,老实本分了一辈子,
也要强了一辈子。他平时有事不求别人,但别人有事,他还会主动去帮忙,不求回报。
同类推荐
 退婚PUA白眼狼,禁欲军官他真香(沈俊彦陆擎川)好看的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推荐退婚PUA白眼狼,禁欲军官他真香沈俊彦陆擎川
退婚PUA白眼狼,禁欲军官他真香(沈俊彦陆擎川)好看的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推荐退婚PUA白眼狼,禁欲军官他真香沈俊彦陆擎川
慕容书生
 苏芮林海(我们成了祖先)全章节在线阅读_(我们成了祖先)完结版免费阅读
苏芮林海(我们成了祖先)全章节在线阅读_(我们成了祖先)完结版免费阅读
雄鸡凤凰
 玄学大师穿成霸总里的扫地僧宫斗宅斗祝昶新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玄学大师穿成霸总里的扫地僧(宫斗宅斗祝昶)
玄学大师穿成霸总里的扫地僧宫斗宅斗祝昶新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玄学大师穿成霸总里的扫地僧(宫斗宅斗祝昶)
余浅生
 血嫁红绣鞋宋言林婉清热门小说阅读_免费完结小说血嫁红绣鞋宋言林婉清
血嫁红绣鞋宋言林婉清热门小说阅读_免费完结小说血嫁红绣鞋宋言林婉清
邪恶小军师
 全世界都比不过我的小竹马(江屿林辰)全章节在线阅读_江屿林辰全章节在线阅读
全世界都比不过我的小竹马(江屿林辰)全章节在线阅读_江屿林辰全章节在线阅读
陌上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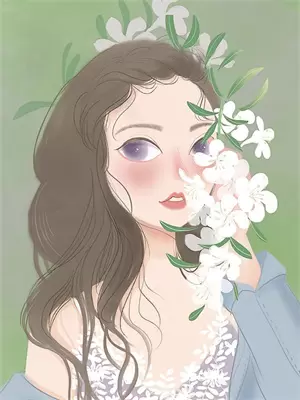 春腾生长时冰冷林小满全文阅读免费全集_最新全本小说春腾生长时(冰冷林小满)
春腾生长时冰冷林小满全文阅读免费全集_最新全本小说春腾生长时(冰冷林小满)
泔水的硕妃
 教育公平(保送内定后我退学让全市震动了)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保送内定后我退学让全市震动了完整版免费在线阅读
教育公平(保送内定后我退学让全市震动了)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保送内定后我退学让全市震动了完整版免费在线阅读
快乐的小皮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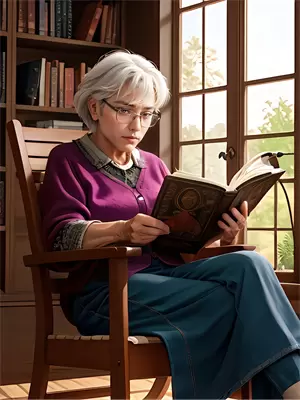 被PPT砸死后我成了规则制定者(冰冷怨念)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推荐被PPT砸死后我成了规则制定者冰冷怨念
被PPT砸死后我成了规则制定者(冰冷怨念)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推荐被PPT砸死后我成了规则制定者冰冷怨念
第根号三支羽毛
 恐游大boss是我网恋前男友游乐幽幽完结好看小说_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恐游大boss是我网恋前男友(游乐幽幽)
恐游大boss是我网恋前男友游乐幽幽完结好看小说_无弹窗全文免费阅读恐游大boss是我网恋前男友(游乐幽幽)
m糖炒冰栗子
 小三将爸爸当活靶子后,我杀疯了(宋墨晴顾翰章)在哪看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小三将爸爸当活靶子后,我杀疯了(宋墨晴顾翰章)
小三将爸爸当活靶子后,我杀疯了(宋墨晴顾翰章)在哪看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小三将爸爸当活靶子后,我杀疯了(宋墨晴顾翰章)
浮清鱼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