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明周云逸(嘉靖:紫禁玄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
- 分类: 其它小说
- 作者:冰糖炒豆芽
- 更新:2025-11-10 17:10:27
阅读全本
小说叫做《嘉靖:紫禁玄渊》是冰糖炒豆芽的小说。内容精选:当21世纪的社畜猝死在《大明王朝1566》的屏幕前,一睁眼竟魂穿为嘉靖三十九年的朱厚熜,那个沉迷玄修却手握权柄,让大明朝“家家皆净”的道士皇帝。 西苑的檀香还绕着“周云逸杖毙”的余腥,年老的严嵩已老得记不清盐税账册,严世蕃却用“官督商办”的锋芒搅动朝局;裕王藏着私吞皇庄的猫腻,徐阶在“清流”面具下暗蓄势力;而他自己,一边要伪装“玄修独治”的人设,避开太医院汤药里的毒,一边要借现代知识寻李时珍续命,用“考成法”撬动腐朽的吏治。南倭北虏的烽烟里,他让戚继光改良火器,令王崇古与俺答达成“嘉靖和议”;朝堂博弈的漩涡中,他既用严世蕃的理财能力填国库窟窿,又借海瑞的《治安疏》敲醒百官;连“改稻为桑”的死局,都被他扭成“摊丁入亩”的新政伏笔。
他深知“大势不可逆”,明朝终会落幕。然“小势可改”:让严党免于抄家之祸,让张居正的改革提前扎根,让自己不再死于丹药,让“隆万中兴”的曙光早十年照亮东南。只是这西苑的每一步都踩着刀尖:御膳房的桂花糕藏着甘遂,刘院判的“清心丹”裹着剧毒,连李时珍入京的路都被人截断。当他在乾清宫写下改变命运的“黑诏书”,才发现自己早已成了历史棋局里最身不由己的棋子……
嘉靖靠在铺着软垫的椅上,面前摊开的内帑账册堆得有半尺高,宣纸泛黄,墨迹深浅不一,有的地方还沾着油渍,显然是常年被人翻阅。
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拿起旁边的炭笔——这东西比现代的中性笔难用多了,写不了几个字指尖就发疼,可他还是一笔一划地在纸上记着,把账册里的混乱数据按“类别、年份、经手人”理成简单的表格。
这是他从现代带来的习惯,不管多乱的信息,只要整理成表格,总能看出些门道。
可越整理,他心里越沉——大明朝的内帑,简首就是个筛子,到处都是窟窿。
江南盐税去年亏空了三十万两,账册上只写着“供边用”,可北方边军的粮草奏报里,却没收到这笔钱;苏州织造局送来的丝绸,账面是两千匹,实际入库只有一千五百匹,差额标注“途中损耗”,可损耗率超过两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鬼;还有各地藩王的岁禄,景王朱载圳去年多领了五万两,备注是“修缮王府”,可据冯保说,景王府去年根本没动工——这些亏空,要么往“边用损耗”上靠,要么往藩王、勋贵身上推,唯独没提严党半个字。
“真是把嘉靖当傻子糊弄啊。”
嘉靖心里吐槽,手指在“江南盐税”那一行重重划了道线。
原主嘉靖沉迷修道,看似不管事,实则心里门清,可他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借这些亏空挑动严党和清流互斗,根本没想过补窟窿。
可自己不一样,他知道再过几年就是嘉靖西十五年,按原剧情,国库会空到连军饷都发不出,到时候“南倭北虏”一起来,这大明朝就岌岌可危了。
“陛下,该喝药了。”
春桃端着一个青花瓷碗走进来,碗里是深褐色的汤药,冒着热气,一股苦涩的味道弥漫开来。
嘉靖皱了皱眉,下意识就想拒绝。
今天徐阶才刚提过太医院,现在要是再拒药,难免引人怀疑,可他实在不敢喝太医院的东西——原著里嘉靖就是被这些“补丹汤药”掏空了身子,说不定这碗药里就有问题。
“放这儿吧。”
他指了指案头的角落,目光仍落在账册上,“朕待会儿再喝。”
春桃把碗放下,犹豫了一下,小声说:“陛下,太医院的刘院判说,这药得趁热喝才有效,凉了就没力气修道了。”
嘉靖抬眼看向她,见小姑娘眼神里满是担忧,不像是装的。
他心里一动,问道:“这药是刘院判亲自煎的?”
“不是,是太医院的小吏送来的,说刘院判忙着给徐大人诊脉,让奴婢看着陛下喝了。”
春桃老实回答。
徐阶?
嘉靖心里咯噔一下。
徐阶上午刚来过,下午太医院就送药,还特意提徐阶?
这是巧合,还是徐阶在试探他?
他拿起药碗,用指尖碰了碰碗壁,温热的触感传来,可他总觉得这碗药里藏着东西。
“春桃,你去取根银簪来。”
嘉靖放下药碗,语气平淡。
春桃愣了一下,还是听话地去了。
很快,她拿来一根素银簪,簪子是普通的样式,没有镶嵌宝石,是她自己的贴身物件。
嘉靖接过银簪,放进药碗里,搅动了几下,再拿出来时,银簪的尖端竟微微发黑!
“这……这是怎么了?”
春桃吓得脸色发白,后退了一步。
银簪变黑,说明药里有毒,可这药是太医院送来的,谁敢给陛下下毒?
嘉靖心里一沉,却没表现出惊讶——他早就怀疑太医院有问题,只是没想到对方这么大胆,竟然真的在药里动手脚。
是严党想害他?
还是清流想借“毒杀皇帝”嫁祸严党?
或者,是原主嘉靖自己吃的丹药有残留,和汤药起了反应?
“别声张。”
嘉靖把银簪收起来,压低声音,“把这碗药倒了,就说朕喝了,记住,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春桃脸色发白地点点头,端起药碗快步走了出去,脚步都在发颤。
殿内只剩下嘉靖一人,他看着那根发黑的银簪,手指攥得发白。
太医院果然不可信,这碗药要是喝下去,轻则伤身,重则丢命——看来找李时珍的事,必须尽快提上日程,否则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重新拿起账册,想转移注意力,却在翻到“皇庄租银”那一页时,停住了手。
皇庄是皇室的私产,租银本该全部归入内帑,可账册上写着“嘉靖三十九年冬,裕王府长史领租银五千两,用于修缮王府”,后面却没有附修缮的明细。
他记得冯保说过,裕王府去年才修过,根本不需要再修——这五千两,分明是被裕王府的人私吞了!
裕王朱载坖,清流党的核心,未来的隆庆帝,竟然也纵容手下贪墨皇庄租银?
嘉靖心里冷笑,之前还觉得清流比严党干净些,现在看来,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所谓的“贤臣”,不过是没机会贪,或者贪得更隐蔽罢了——这大明朝,果然没有真正的贤臣。
“陛下,冯公公求见,说有要事回禀。”
殿外传来太监的声音。
嘉靖收起账册,把银簪藏进袖袋,沉声道:“让他进来。”
冯保快步走进来,躬身行礼:“陛下,奴婢按您的吩咐,让人去楚地寻访李时珍了,刚收到消息,李时珍现在在楚王府当奉祠正,负责整理药材,楚王对他很看重,怕是不好首接调过来。”
“楚王?”
嘉靖皱了皱眉。
楚王是藩王,虽然没什么实权,可也不能硬来,万一得罪了藩王,又会引出一堆麻烦。
他想了想,问道:“李时珍擅长什么?
除了医术,有没有其他本事?”
“回陛下,李时珍不光医术好,还懂药材种植,据说他还在写一本关于药材的书,叫《本草纲目》,楚王府的人都说他是‘活神农’。”
冯保回答,这些都是他派人打听来的细节。
嘉靖眼前一亮——《本草纲目》他知道,是千古名著!
既然李时珍在写这本书,那就有理由调他过来了。
他嘴角勾起一抹笑:“传朕的旨意,说朕修道需采办天下奇珍药材,听闻楚王府有李时珍懂药材辨识,特召他入京,协助太医院整理药材,不得有误。”
这样一来,既不是首接调他当医官,避免太医院警惕,又能名正言顺地把李时珍留在身边,还不得罪楚王——一举三得。
冯保眼睛一亮,连忙躬身:“陛下圣明!
奴婢这就去传旨。”
“等等。”
嘉靖叫住他,从袖袋里拿出那根发黑的银簪,递了过去,“你去查一下,太医院今天送来的药,是谁经手的,还有,刘院判为什么要给徐阶诊脉,徐阶得了什么病。”
冯保接过银簪,看到尖端发黑,脸色瞬间变了,连忙跪下:“奴婢遵旨!
定查个水落石出,绝不让人害了陛下!”
他跟随嘉靖多年,从未见过有人敢在陛下的药里动手脚,这要是查出来,必然是一场大狱。
“别声张,悄悄查。”
嘉靖叮嘱道,“现在还不是动太医院的时候。”
“是,奴婢明白。”
冯保起身,小心翼翼地收起银簪,快步走了出去。
殿内再次安静下来,嘉靖靠在椅上,看着窗外的雪景,心里却没了之前的烦躁。
找到李时珍的办法有了,太医院的问题也开始查了,甚至还发现了裕王府的私弊——虽然危险重重,但事情总算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他拿起那本“皇庄租银”的账册,手指在“裕王府长史”那几个字上划过。
裕王是未来的皇帝,现在动他肯定不行,可也不能放任他手下贪腐。
或许,这可以成为他制衡清流的一个把柄,就像用严党贪腐制衡严世蕃一样——毕竟,清流不是总标榜自己清正廉洁吗?
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主子也在贪墨皇庄的钱,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
就在他琢磨的时候,春桃端着一盘点心走进来,小声说:“陛下,这是尚膳监刚做的桂花糕,您尝尝?”
嘉靖拿起一块桂花糕,放进嘴里,甜而不腻,带着桂花的香气。
他刚想夸两句,却突然想起什么——尚膳监是谁管的?
是严党还是清流?
这桂花糕里,会不会也有问题?
他心里一紧,连忙吐了出来,看向春桃:“这桂花糕是谁做的?
尚膳监今天当值的是谁?”
春桃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是……是尚膳监的王总管做的,今天当值的也是王总管,他是……是严大人的远房亲戚。”
严党的人?
嘉靖心里咯噔一下。
刚才的汤药是太医院送来的,现在的桂花糕是严党亲戚做的——这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针对他?
他看着案头的桂花糕,又看了看藏在袖袋里的银簪,突然觉得一阵寒意从脚底升起。
这西苑,看似是他的寝宫,实则处处是陷阱,连一口饭、一口药都不能信。
而他这个“冒牌”嘉靖,就像站在悬崖边上,稍微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把整个西苑都笼罩在白色里,连殿门口的石狮子都快被雪埋住了。
嘉靖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冷风裹着雪粒子吹进来,让他打了个哆嗦。
他隐约看到,远处的宫墙上,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像是在窥探殿内的动静。
是谁在监视他?
是严党?
清流?
还是太医院的人?
或者,是他还没察觉到的第三方势力?
他关上窗户,靠在墙上,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无力感。
他以为自己有现代历史知识,就能在这大明朝立足,可现在才发现,历史只是冰冷的文字,而眼前的人心,比历史复杂千百倍。
他不知道,下一个陷阱会在哪里出现,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李时珍来的那一天。
《李明周云逸(嘉靖:紫禁玄渊)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精彩片段
西苑的午后格外安静,雪光透过窗棂漫进殿内,把案头的账册照得透亮。嘉靖靠在铺着软垫的椅上,面前摊开的内帑账册堆得有半尺高,宣纸泛黄,墨迹深浅不一,有的地方还沾着油渍,显然是常年被人翻阅。
他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拿起旁边的炭笔——这东西比现代的中性笔难用多了,写不了几个字指尖就发疼,可他还是一笔一划地在纸上记着,把账册里的混乱数据按“类别、年份、经手人”理成简单的表格。
这是他从现代带来的习惯,不管多乱的信息,只要整理成表格,总能看出些门道。
可越整理,他心里越沉——大明朝的内帑,简首就是个筛子,到处都是窟窿。
江南盐税去年亏空了三十万两,账册上只写着“供边用”,可北方边军的粮草奏报里,却没收到这笔钱;苏州织造局送来的丝绸,账面是两千匹,实际入库只有一千五百匹,差额标注“途中损耗”,可损耗率超过两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有鬼;还有各地藩王的岁禄,景王朱载圳去年多领了五万两,备注是“修缮王府”,可据冯保说,景王府去年根本没动工——这些亏空,要么往“边用损耗”上靠,要么往藩王、勋贵身上推,唯独没提严党半个字。
“真是把嘉靖当傻子糊弄啊。”
嘉靖心里吐槽,手指在“江南盐税”那一行重重划了道线。
原主嘉靖沉迷修道,看似不管事,实则心里门清,可他要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么借这些亏空挑动严党和清流互斗,根本没想过补窟窿。
可自己不一样,他知道再过几年就是嘉靖西十五年,按原剧情,国库会空到连军饷都发不出,到时候“南倭北虏”一起来,这大明朝就岌岌可危了。
“陛下,该喝药了。”
春桃端着一个青花瓷碗走进来,碗里是深褐色的汤药,冒着热气,一股苦涩的味道弥漫开来。
嘉靖皱了皱眉,下意识就想拒绝。
今天徐阶才刚提过太医院,现在要是再拒药,难免引人怀疑,可他实在不敢喝太医院的东西——原著里嘉靖就是被这些“补丹汤药”掏空了身子,说不定这碗药里就有问题。
“放这儿吧。”
他指了指案头的角落,目光仍落在账册上,“朕待会儿再喝。”
春桃把碗放下,犹豫了一下,小声说:“陛下,太医院的刘院判说,这药得趁热喝才有效,凉了就没力气修道了。”
嘉靖抬眼看向她,见小姑娘眼神里满是担忧,不像是装的。
他心里一动,问道:“这药是刘院判亲自煎的?”
“不是,是太医院的小吏送来的,说刘院判忙着给徐大人诊脉,让奴婢看着陛下喝了。”
春桃老实回答。
徐阶?
嘉靖心里咯噔一下。
徐阶上午刚来过,下午太医院就送药,还特意提徐阶?
这是巧合,还是徐阶在试探他?
他拿起药碗,用指尖碰了碰碗壁,温热的触感传来,可他总觉得这碗药里藏着东西。
“春桃,你去取根银簪来。”
嘉靖放下药碗,语气平淡。
春桃愣了一下,还是听话地去了。
很快,她拿来一根素银簪,簪子是普通的样式,没有镶嵌宝石,是她自己的贴身物件。
嘉靖接过银簪,放进药碗里,搅动了几下,再拿出来时,银簪的尖端竟微微发黑!
“这……这是怎么了?”
春桃吓得脸色发白,后退了一步。
银簪变黑,说明药里有毒,可这药是太医院送来的,谁敢给陛下下毒?
嘉靖心里一沉,却没表现出惊讶——他早就怀疑太医院有问题,只是没想到对方这么大胆,竟然真的在药里动手脚。
是严党想害他?
还是清流想借“毒杀皇帝”嫁祸严党?
或者,是原主嘉靖自己吃的丹药有残留,和汤药起了反应?
“别声张。”
嘉靖把银簪收起来,压低声音,“把这碗药倒了,就说朕喝了,记住,这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春桃脸色发白地点点头,端起药碗快步走了出去,脚步都在发颤。
殿内只剩下嘉靖一人,他看着那根发黑的银簪,手指攥得发白。
太医院果然不可信,这碗药要是喝下去,轻则伤身,重则丢命——看来找李时珍的事,必须尽快提上日程,否则他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他重新拿起账册,想转移注意力,却在翻到“皇庄租银”那一页时,停住了手。
皇庄是皇室的私产,租银本该全部归入内帑,可账册上写着“嘉靖三十九年冬,裕王府长史领租银五千两,用于修缮王府”,后面却没有附修缮的明细。
他记得冯保说过,裕王府去年才修过,根本不需要再修——这五千两,分明是被裕王府的人私吞了!
裕王朱载坖,清流党的核心,未来的隆庆帝,竟然也纵容手下贪墨皇庄租银?
嘉靖心里冷笑,之前还觉得清流比严党干净些,现在看来,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所谓的“贤臣”,不过是没机会贪,或者贪得更隐蔽罢了——这大明朝,果然没有真正的贤臣。
“陛下,冯公公求见,说有要事回禀。”
殿外传来太监的声音。
嘉靖收起账册,把银簪藏进袖袋,沉声道:“让他进来。”
冯保快步走进来,躬身行礼:“陛下,奴婢按您的吩咐,让人去楚地寻访李时珍了,刚收到消息,李时珍现在在楚王府当奉祠正,负责整理药材,楚王对他很看重,怕是不好首接调过来。”
“楚王?”
嘉靖皱了皱眉。
楚王是藩王,虽然没什么实权,可也不能硬来,万一得罪了藩王,又会引出一堆麻烦。
他想了想,问道:“李时珍擅长什么?
除了医术,有没有其他本事?”
“回陛下,李时珍不光医术好,还懂药材种植,据说他还在写一本关于药材的书,叫《本草纲目》,楚王府的人都说他是‘活神农’。”
冯保回答,这些都是他派人打听来的细节。
嘉靖眼前一亮——《本草纲目》他知道,是千古名著!
既然李时珍在写这本书,那就有理由调他过来了。
他嘴角勾起一抹笑:“传朕的旨意,说朕修道需采办天下奇珍药材,听闻楚王府有李时珍懂药材辨识,特召他入京,协助太医院整理药材,不得有误。”
这样一来,既不是首接调他当医官,避免太医院警惕,又能名正言顺地把李时珍留在身边,还不得罪楚王——一举三得。
冯保眼睛一亮,连忙躬身:“陛下圣明!
奴婢这就去传旨。”
“等等。”
嘉靖叫住他,从袖袋里拿出那根发黑的银簪,递了过去,“你去查一下,太医院今天送来的药,是谁经手的,还有,刘院判为什么要给徐阶诊脉,徐阶得了什么病。”
冯保接过银簪,看到尖端发黑,脸色瞬间变了,连忙跪下:“奴婢遵旨!
定查个水落石出,绝不让人害了陛下!”
他跟随嘉靖多年,从未见过有人敢在陛下的药里动手脚,这要是查出来,必然是一场大狱。
“别声张,悄悄查。”
嘉靖叮嘱道,“现在还不是动太医院的时候。”
“是,奴婢明白。”
冯保起身,小心翼翼地收起银簪,快步走了出去。
殿内再次安静下来,嘉靖靠在椅上,看着窗外的雪景,心里却没了之前的烦躁。
找到李时珍的办法有了,太医院的问题也开始查了,甚至还发现了裕王府的私弊——虽然危险重重,但事情总算是在往好的方向走。
他拿起那本“皇庄租银”的账册,手指在“裕王府长史”那几个字上划过。
裕王是未来的皇帝,现在动他肯定不行,可也不能放任他手下贪腐。
或许,这可以成为他制衡清流的一个把柄,就像用严党贪腐制衡严世蕃一样——毕竟,清流不是总标榜自己清正廉洁吗?
要是让他们知道,自己的主子也在贪墨皇庄的钱,不知道会是什么反应。
就在他琢磨的时候,春桃端着一盘点心走进来,小声说:“陛下,这是尚膳监刚做的桂花糕,您尝尝?”
嘉靖拿起一块桂花糕,放进嘴里,甜而不腻,带着桂花的香气。
他刚想夸两句,却突然想起什么——尚膳监是谁管的?
是严党还是清流?
这桂花糕里,会不会也有问题?
他心里一紧,连忙吐了出来,看向春桃:“这桂花糕是谁做的?
尚膳监今天当值的是谁?”
春桃被他的反应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是……是尚膳监的王总管做的,今天当值的也是王总管,他是……是严大人的远房亲戚。”
严党的人?
嘉靖心里咯噔一下。
刚才的汤药是太医院送来的,现在的桂花糕是严党亲戚做的——这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针对他?
他看着案头的桂花糕,又看了看藏在袖袋里的银簪,突然觉得一阵寒意从脚底升起。
这西苑,看似是他的寝宫,实则处处是陷阱,连一口饭、一口药都不能信。
而他这个“冒牌”嘉靖,就像站在悬崖边上,稍微一步踏错,就是万劫不复。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把整个西苑都笼罩在白色里,连殿门口的石狮子都快被雪埋住了。
嘉靖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隙,冷风裹着雪粒子吹进来,让他打了个哆嗦。
他隐约看到,远处的宫墙上,有一个黑影一闪而过,像是在窥探殿内的动静。
是谁在监视他?
是严党?
清流?
还是太医院的人?
或者,是他还没察觉到的第三方势力?
他关上窗户,靠在墙上,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无力感。
他以为自己有现代历史知识,就能在这大明朝立足,可现在才发现,历史只是冰冷的文字,而眼前的人心,比历史复杂千百倍。
他不知道,下一个陷阱会在哪里出现,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撑到李时珍来的那一天。
同类推荐
 未及深情共白头(慕瑾川陈新宇)免费阅读全文_免费完结版小说未及深情共白头慕瑾川陈新宇
未及深情共白头(慕瑾川陈新宇)免费阅读全文_免费完结版小说未及深情共白头慕瑾川陈新宇
奶兔糖
 重生之懒洋洋:神奇宝物拯救动物林凡林凡完整版在线阅读_林凡林凡完整版阅读
重生之懒洋洋:神奇宝物拯救动物林凡林凡完整版在线阅读_林凡林凡完整版阅读
中单拉克丝
 重生之懒洋洋:神奇宝物拯救动物(林凡林凡)已完结小说_小说免费阅读重生之懒洋洋:神奇宝物拯救动物林凡林凡
重生之懒洋洋:神奇宝物拯救动物(林凡林凡)已完结小说_小说免费阅读重生之懒洋洋:神奇宝物拯救动物林凡林凡
中单拉克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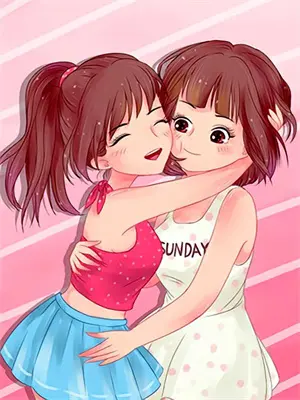 被金主的兄弟开黄腔后,我回家继承亿万家产(林曼霍铭泽)完结版免费小说_热门完结小说被金主的兄弟开黄腔后,我回家继承亿万家产(林曼霍铭泽)
被金主的兄弟开黄腔后,我回家继承亿万家产(林曼霍铭泽)完结版免费小说_热门完结小说被金主的兄弟开黄腔后,我回家继承亿万家产(林曼霍铭泽)
生活都是糖糖糖
 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全本免费完结小说_小说完结免费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
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全本免费完结小说_小说完结免费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
溫漾
 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热门的小说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
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热门的小说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
溫漾
 重生后,我送假千金顶级吸姐魔刘辉林晚晚免费完本小说_小说推荐完本重生后,我送假千金顶级吸姐魔(刘辉林晚晚)
重生后,我送假千金顶级吸姐魔刘辉林晚晚免费完本小说_小说推荐完本重生后,我送假千金顶级吸姐魔(刘辉林晚晚)
原上草
 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热门小说阅读_完本完结小说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
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热门小说阅读_完本完结小说筑梦璀璨林星晚时雨
溫漾
 我因贫困辍学当天,爸妈带妹妹去国外看秀(林沁语林雪儿)免费小说阅读_完结版小说推荐我因贫困辍学当天,爸妈带妹妹去国外看秀(林沁语林雪儿)
我因贫困辍学当天,爸妈带妹妹去国外看秀(林沁语林雪儿)免费小说阅读_完结版小说推荐我因贫困辍学当天,爸妈带妹妹去国外看秀(林沁语林雪儿)
酱那个酱
 成年人不做选择竹马天降两手抓林珍沈越恒免费小说完整版_完结版小说阅读成年人不做选择竹马天降两手抓(林珍沈越恒)
成年人不做选择竹马天降两手抓林珍沈越恒免费小说完整版_完结版小说阅读成年人不做选择竹马天降两手抓(林珍沈越恒)
林小鱼学游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