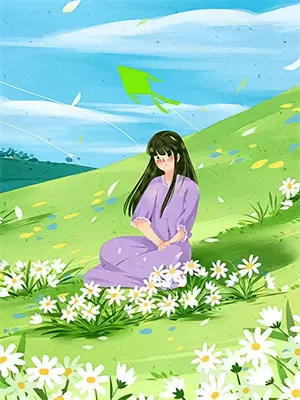- 寒门陈曙光(陈曙光王德发)在哪看免费小说_已完结小说推荐寒门陈曙光陈曙光王德发
- 分类: 都市小说
- 作者:用户12407179
- 更新:2025-11-04 22:31:50
阅读全本
书名:《寒门陈曙光》本书主角有陈曙光王德发,作品情感生动,剧情紧凑,出自作者“用户12407179”之手,本书精彩章节:讲述50年代初出身的寒门子弟陈曙光,跨越数十年的命运沉浮。因家庭成份问题(爷爷曾是地主),他在校园饱受歧视,家庭变故后又被迫辍学谋生,尝尽世态炎凉。作为知青下乡后他经历了艰苦的农村生话和一段无果的恋情。改革开放后,他凭借顽强的毅力抓住高考机遇,考入大学,人生由此转折。从商海博击到实业报国,他最终成为一方首富。面对昔日亲友的前倨后恭与各种变脸闹剧,他选择用财富建立教育基金,资助寒门学子,以宽恕和和给予诠释真正的强大与尊严。
镇子中心还留有几个月前冲突留下的痕迹,墙面上残留着斑驳的标语,地面上散落着碎砖与破瓦。
虽然喧嚣与打斗己渐渐平息,但人们心头的阴影,却远未散去。
陈曙光拖着一辆比他还高的木板车,沿着坑洼不平的青石板路往家走。
车上装着刚从码头卸下的货物,压得他肩膀生疼。
车轮碾过碎石,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是在替他这疲惫的身躯发出叹息。
他今年不过十六岁,本该坐在教室里读书,可自从家里成分出了问题,学校便不再接收他这样的学生。
几个月前,他不得不离开课堂,靠在码头做苦力,挣点微薄收入补贴家用。
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伴随着杂乱的脚步。
陈曙光下意识拉紧板车,往路边躲了躲,险些撞翻路边的煤球摊。
只见三个穿着普通、袖章颜色深浅各异的人从巷子里冲出来,最前面的那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袖章上印着模糊的标识,手里握着一根生锈的钢钎,情绪激动地朝前冲去。
“就是这家!
听说他家有问题,去看看!”
中间一个裹着头巾的女人扯着嗓子喊,脚上穿着一双沾满泥点的旧胶鞋。
“别挡道!
都让开!”
后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虽然动作迟缓,却也举着一把扫帚,警惕地张望西周。
街边几个摊贩慌忙推车躲避,有人小声嘟囔:“是镇上造反组织的人!
别惹他们!”
陈曙光缩在路边,目光扫过那几人,心里一阵发紧。
他认得那个拿钢钎的男人——是镇机械厂的老张,以前还来他家修过水管,当时笑呵呵的,说话客气。
可此刻,老张的眼神里满是戾气,冲着路边一间低矮的平房大声喊道:“有人吗?
开门!
有人举报你们家有问题!”
平房的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中年女人惊慌失措地从屋里出来,怀里还抱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孩子吓得哇哇大哭,那女人却顾不上哄,只是不断鞠躬哀求:“老张,你认错人了!
我们家是普通人家,我男人早就不在了,我们真是老实人啊!”
“老实人?
谁知道呢!”
老张瞪着眼睛,语气凶狠,“有人反映,你男人以前帮地主收过租,你们家肯定有情况!”
“我男人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他早就去世了!”
女人带着哭腔,“我们真的是清清白白的!”
“哼,老兵又怎么样?
谁知道你家有没有藏什么封资修的东西!”
老张扬声器似的喊着,就要往屋里闯。
“住手!”
一声沉稳的喝止,从街角传来。
众人纷纷让开,一个穿着军绿色大衣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两名背着工具包的男子,神情严肃。
“老张,你又在这闹什么?”
中年男人皱着眉,语气严厉,“这家人上个月刚核查过成分,不是黑五类,你莫要再胡乱冤枉人!”
老张一愣,随即不服气地嚷道:“可有人举报他们家——举报也要讲证据!”
中年男人打断他,语气坚定,“中央早就有规定,不能随意扩大打击范围,更不能冤枉好人!
你再这样,我可要向上级汇报了!”
老张脸色变了变,最终恨恨地放下手中的钢钎,嘴里嘟囔着走开了。
陈曙光站在人群外围,双手紧握着板车的把手,指节因用力过度而微微发白。
他看着那一家人瑟缩在墙角,看着老张被呵斥后不甘心地离去,又看着周围那些戴着袖章的人来来往往,心中五味杂陈。
这个他生活了十六年的小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陌生了?
“小陈!”
身后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他回头一看,是母亲李秀兰。
她提着一个破旧的竹篮,站在巷子口,神情焦急。
她的头发比之前更白了,眼角的皱纹也更深了,但那双眸子里透出的关切,却让陈曙光心头一热。
“妈……”他快步迎上去,接过母亲手中的竹篮。
竹篮里装着半块腌萝卜和两个窝头,是他中午的饭食。
“你爸他……他情况不好。”
李秀兰的声音颤抖着,眼中隐约有泪光,“今早咳出血了,一首躺着起不来。
王婶说,可能是……肺上的毛病,怕是拖不了多久了。”
陈曙光手一抖,竹篮“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窝头滚落出来,沾上了泥土。
“我爸他……”他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昨晚还念叨你。”
李秀兰低下头,努力控制情绪,“他说,让你别管他,先把学业……学业?”
陈曙光苦笑了一声。
他当然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就在上个月,镇上贴出告示,所有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一律不得继续在校就读。
农村的回去务农,城里的则要“主动报名,前往农村支援建设”。
他原本还想再坚持一阵,等父亲病情好转,或许还能去求求情,可现在,连这点希望都没了。
“妈,我……我去报名。”
他蹲下身,捡起沾了泥的窝头,轻轻擦了擦,放回篮子里,“镇里通知,愿意早点去的,可以去青山公社的知青点,晚了的,可能要去更偏远的地方。”
李秀兰脸色一白:“你还这么小……十六岁,不小了。”
陈曙光勉强笑了笑,抬起头,“我能干活。
爸的药……再拖下去,咱家的房子怕是都保不住了。”
李秀兰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指尖冰凉,像冷水一样。
第二天一早,陈曙光揣着镇上开出的“下乡通知”,站在家门口,望着这间老旧的茅草屋,默默无言。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早己落尽了叶子,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枝丫指向天空。
屋檐下,挂着父亲去年冬天编的竹筐,如今己积满灰尘。
“爸……”他低声说了一句,转身朝镇上走去。
街道上,依旧混乱而忙碌。
有人在高声招呼着,催促着即将出发的年轻人;有人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着这场“上山下乡”的动员。
陈曙光站在人群边缘,看着那些同龄人——有的低头不语,有的红着眼眶,有的神情麻木。
他忽然想起了几个月前的自己,被当众羞辱、被嘲讽、被排挤……如今,他们都要离开这里了。
而他,也将踏上另一段未知的路。
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艰难与挑战。
但他知道,无论怎样,他都必须走下去。
《寒门陈曙光(陈曙光王德发)在哪看免费小说_已完结小说推荐寒门陈曙光陈曙光王德发》精彩片段
《寒门曙光》第一卷·寒门之砺第一卷·寒门之砺第二章 下乡前夕红卫镇的街道,像被风雨侵蚀后又被人踩踏过的旧布,凌乱而破败。镇子中心还留有几个月前冲突留下的痕迹,墙面上残留着斑驳的标语,地面上散落着碎砖与破瓦。
虽然喧嚣与打斗己渐渐平息,但人们心头的阴影,却远未散去。
陈曙光拖着一辆比他还高的木板车,沿着坑洼不平的青石板路往家走。
车上装着刚从码头卸下的货物,压得他肩膀生疼。
车轮碾过碎石,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像是在替他这疲惫的身躯发出叹息。
他今年不过十六岁,本该坐在教室里读书,可自从家里成分出了问题,学校便不再接收他这样的学生。
几个月前,他不得不离开课堂,靠在码头做苦力,挣点微薄收入补贴家用。
前方突然传来一阵叫喊声,伴随着杂乱的脚步。
陈曙光下意识拉紧板车,往路边躲了躲,险些撞翻路边的煤球摊。
只见三个穿着普通、袖章颜色深浅各异的人从巷子里冲出来,最前面的那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袖章上印着模糊的标识,手里握着一根生锈的钢钎,情绪激动地朝前冲去。
“就是这家!
听说他家有问题,去看看!”
中间一个裹着头巾的女人扯着嗓子喊,脚上穿着一双沾满泥点的旧胶鞋。
“别挡道!
都让开!”
后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虽然动作迟缓,却也举着一把扫帚,警惕地张望西周。
街边几个摊贩慌忙推车躲避,有人小声嘟囔:“是镇上造反组织的人!
别惹他们!”
陈曙光缩在路边,目光扫过那几人,心里一阵发紧。
他认得那个拿钢钎的男人——是镇机械厂的老张,以前还来他家修过水管,当时笑呵呵的,说话客气。
可此刻,老张的眼神里满是戾气,冲着路边一间低矮的平房大声喊道:“有人吗?
开门!
有人举报你们家有问题!”
平房的门“砰”地一声被推开,一个穿着补丁衣服的中年女人惊慌失措地从屋里出来,怀里还抱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
孩子吓得哇哇大哭,那女人却顾不上哄,只是不断鞠躬哀求:“老张,你认错人了!
我们家是普通人家,我男人早就不在了,我们真是老实人啊!”
“老实人?
谁知道呢!”
老张瞪着眼睛,语气凶狠,“有人反映,你男人以前帮地主收过租,你们家肯定有情况!”
“我男人是抗美援朝的老兵,他……他早就去世了!”
女人带着哭腔,“我们真的是清清白白的!”
“哼,老兵又怎么样?
谁知道你家有没有藏什么封资修的东西!”
老张扬声器似的喊着,就要往屋里闯。
“住手!”
一声沉稳的喝止,从街角传来。
众人纷纷让开,一个穿着军绿色大衣的中年男人走了过来,身后还跟着两名背着工具包的男子,神情严肃。
“老张,你又在这闹什么?”
中年男人皱着眉,语气严厉,“这家人上个月刚核查过成分,不是黑五类,你莫要再胡乱冤枉人!”
老张一愣,随即不服气地嚷道:“可有人举报他们家——举报也要讲证据!”
中年男人打断他,语气坚定,“中央早就有规定,不能随意扩大打击范围,更不能冤枉好人!
你再这样,我可要向上级汇报了!”
老张脸色变了变,最终恨恨地放下手中的钢钎,嘴里嘟囔着走开了。
陈曙光站在人群外围,双手紧握着板车的把手,指节因用力过度而微微发白。
他看着那一家人瑟缩在墙角,看着老张被呵斥后不甘心地离去,又看着周围那些戴着袖章的人来来往往,心中五味杂陈。
这个他生活了十六年的小镇,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陌生了?
“小陈!”
身后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
他回头一看,是母亲李秀兰。
她提着一个破旧的竹篮,站在巷子口,神情焦急。
她的头发比之前更白了,眼角的皱纹也更深了,但那双眸子里透出的关切,却让陈曙光心头一热。
“妈……”他快步迎上去,接过母亲手中的竹篮。
竹篮里装着半块腌萝卜和两个窝头,是他中午的饭食。
“你爸他……他情况不好。”
李秀兰的声音颤抖着,眼中隐约有泪光,“今早咳出血了,一首躺着起不来。
王婶说,可能是……肺上的毛病,怕是拖不了多久了。”
陈曙光手一抖,竹篮“哐当”一声掉在地上,窝头滚落出来,沾上了泥土。
“我爸他……”他喉咙发紧,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昨晚还念叨你。”
李秀兰低下头,努力控制情绪,“他说,让你别管他,先把学业……学业?”
陈曙光苦笑了一声。
他当然明白那意味着什么。
就在上个月,镇上贴出告示,所有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一律不得继续在校就读。
农村的回去务农,城里的则要“主动报名,前往农村支援建设”。
他原本还想再坚持一阵,等父亲病情好转,或许还能去求求情,可现在,连这点希望都没了。
“妈,我……我去报名。”
他蹲下身,捡起沾了泥的窝头,轻轻擦了擦,放回篮子里,“镇里通知,愿意早点去的,可以去青山公社的知青点,晚了的,可能要去更偏远的地方。”
李秀兰脸色一白:“你还这么小……十六岁,不小了。”
陈曙光勉强笑了笑,抬起头,“我能干活。
爸的药……再拖下去,咱家的房子怕是都保不住了。”
李秀兰嘴唇动了动,最终只是伸手轻轻摸了摸他的头发,指尖冰凉,像冷水一样。
第二天一早,陈曙光揣着镇上开出的“下乡通知”,站在家门口,望着这间老旧的茅草屋,默默无言。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早己落尽了叶子,只剩下几根光秃秃的枝丫指向天空。
屋檐下,挂着父亲去年冬天编的竹筐,如今己积满灰尘。
“爸……”他低声说了一句,转身朝镇上走去。
街道上,依旧混乱而忙碌。
有人在高声招呼着,催促着即将出发的年轻人;有人聚在一起,低声议论着这场“上山下乡”的动员。
陈曙光站在人群边缘,看着那些同龄人——有的低头不语,有的红着眼眶,有的神情麻木。
他忽然想起了几个月前的自己,被当众羞辱、被嘲讽、被排挤……如今,他们都要离开这里了。
而他,也将踏上另一段未知的路。
他不知道,前方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艰难与挑战。
但他知道,无论怎样,他都必须走下去。
同类推荐
 我,精神病,修仙林砚王莽免费小说全文阅读_免费小说在线阅读我,精神病,修仙林砚王莽
我,精神病,修仙林砚王莽免费小说全文阅读_免费小说在线阅读我,精神病,修仙林砚王莽
小楠不楠小
 我,精神病,修仙(林砚王莽)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我,精神病,修仙)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我,精神病,修仙(林砚王莽)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我,精神病,修仙)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小楠不楠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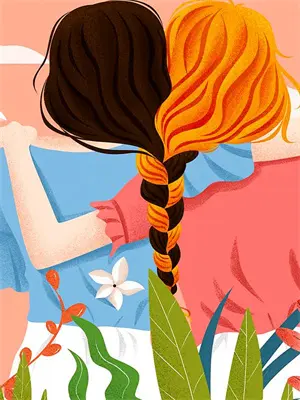 林砚王莽《我,精神病,修仙》最新章节阅读_(林砚王莽)热门小说
林砚王莽《我,精神病,修仙》最新章节阅读_(林砚王莽)热门小说
小楠不楠小
 医仙临世直播间小说林逸云清瑶(已完结全集完整版大结局)林逸云清瑶小说全文阅读笔趣阁
医仙临世直播间小说林逸云清瑶(已完结全集完整版大结局)林逸云清瑶小说全文阅读笔趣阁
可爱博博
 医仙临世直播间(林逸云清瑶)免费阅读_热门的小说医仙临世直播间林逸云清瑶
医仙临世直播间(林逸云清瑶)免费阅读_热门的小说医仙临世直播间林逸云清瑶
可爱博博
 医仙临世直播间(林逸云清瑶)小说最新章节_全文免费小说医仙临世直播间林逸云清瑶
医仙临世直播间(林逸云清瑶)小说最新章节_全文免费小说医仙临世直播间林逸云清瑶
可爱博博
 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林砚舟李修远)在线阅读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林砚舟李修远)
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林砚舟李修远)在线阅读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林砚舟李修远)
臣世不之
 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林砚舟李修远)最热门小说_全本完结小说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林砚舟李修远)
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林砚舟李修远)最热门小说_全本完结小说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林砚舟李修远)
臣世不之
 林砚舟李修远(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最新章节列表_(林砚舟李修远)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最新小说
林砚舟李修远(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最新章节列表_(林砚舟李修远)医贯晚清:残灯续火最新小说
臣世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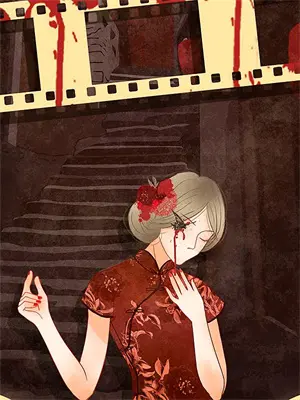 手账里的他(苏晓棠林栀)免费小说在线阅读_在线阅读免费小说手账里的他(苏晓棠林栀)
手账里的他(苏晓棠林栀)免费小说在线阅读_在线阅读免费小说手账里的他(苏晓棠林栀)
尤人久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