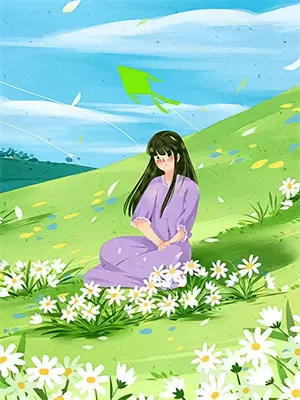- 四大封神.~乐乐复印免费小说完整版_完结版小说阅读四大封神.~(乐乐复印)
- 分类: 悬疑惊悚
- 作者:旧爱书写
- 更新:2025-10-18 21:53:51
《四大封神.~乐乐复印免费小说完整版_完结版小说阅读四大封神.~(乐乐复印)》精彩片段
我去派出所报案,说我们公司的复印机在吃人。接待我的年轻警察皱起了眉头,
记录的手停了一下,抬头看我,
眼神里混合着审视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又来了个神经病”的无奈。“女士,你说具体点,
复印机怎么……吃人?”我深吸一口气,
努力让声音听起来不那么颤抖:“它复印出来的东西,上面会多出一个人影,
一个小孩的影子。而且……而且我儿子说,他晚上能听到那台机器在哭。”警察放下笔,
身体微微后靠,用一种尽量平缓的语气问:“您儿子?他多大了?”“五岁。”我回答。
“所以,是您儿子告诉您,复印机在哭。您自己亲眼见过,或者说……听过吗?”我愣住了。
我没有亲耳听过,但当我深夜加班,独自面对那台老旧机器低沉的运行嗡鸣时,
似乎总能捕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像是小孩抽泣的杂音,混在里面。可我不确定,
那是不是只是机器故障的异响,或者,仅仅是我的错觉。“我……我不确定。”我老实说,
“但是那个人影!警察同志,那个人影是真的!我复印的文件,干干净净,出来的纸上,
角落裡就会多一个模糊的、像小孩子蹲着的身影!一次是巧合,两次是意外,
可这已经连续一个星期了!”我激动地从随身携带的文件夹里抽出一叠文件,摊在桌面上。
那是我最近经手的一些报表和合同复印件。我指着每一张纸的右下角。“看!这里!这里!
还有这里!”警察凑过来,仔细地看着我指的地方,眉头越皱越紧。“女士,”他抬起头,
眼神里的那点耐心几乎消耗殆尽,“这些地方,除了有一些墨粉不均匀造成的污渍,
我什么也没看到。没有您说的小孩影子。”“怎么可能?!”我夺过文件,
低头看去——果然,那些曾经清晰映在我眼中的小小黑影,此刻在派出所明亮的灯光下,
竟然真的变成了一片片毫无意义的、灰蒙蒙的脏污墨点。它们普通得不能再普通,随处可见,
根本无法让人联想到任何孩子的形状。我的血液仿佛瞬间凉了下去。
“不是的……之前明明很清楚的……”我喃喃自语,
巨大的困惑和一种被孤立、被否定的恐慌攫住了我。警察叹了口气:“女士,
您最近工作压力是不是很大?或者……睡眠不太好?您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很难立案。要不,
您先回去休息一下,或者……去看看医生?”他看着我的眼神,已经不再是看一个报案人,
而是在看一个需要帮助的、精神恍惚的病人。那一刻,我知道,他不会相信我了。
没有人会相信一个指着复印机说它吃人的疯子。
可我心里有个声音在尖叫:那台机器一定有问题!它吞掉了什么,正在一点一点地,
吐回这个现实世界。而我的儿子,他是唯一一个,能“听”到那个被吞掉的东西的人。
我拿着那叠“干净”了的文件,失魂落魄地走出派出所。阳光刺眼,我却感觉浑身发冷。
回到公司,我该怎么面对那台机器?今晚,我又该如何向我那五岁的儿子解释,
妈妈没能抓住那个在复印机里哭的“朋友”?而最让我恐惧的是,当我今天早上离开家时,
儿子蹲在客厅角落玩积木,头也不抬地,
用他那种特有的、软糯而清晰的声音对我说:“妈妈,它说……它快要出来了。
”---2:调查与否定我没有听从警察的建议去看医生,而是直接回到了公司。
踏进办公区的那一刻,空调的冷气仿佛带着粘稠的质感,缠绕上来。同事们一如往常地忙碌,
键盘声、电话铃声、低语声交织,一切都显得正常得过分,反而透出一种虚假。
我的目光不受控制地投向走廊尽头那间独立的复印间。门关着,像一只闭着的、沉默的嘴。
“小悦,早上的报表复印好了吗?”部门主管李姐走过来,语气平常地问道。
我的心猛地一跳,强作镇定:“还……还没,李姐。复印机好像有点问题,我正要去看看。
”李姐挑了挑眉,没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尽快哈,总部催得急。
你最近脸色不太好,别太累了。”她的关心在我听来别有深意。
我是不是真的看起来像个疯子?我深吸一口气,走向复印间。推开门,
里面熟悉的墨粉和纸张气味扑面而来,那台老旧的复合机静静地蹲在角落,指示灯熄灭着,
像在沉睡。我打开灯,日光灯管闪烁了两下,才不情愿地亮起,发出嗡嗡的电流声。
我拿起一叠待印的空白A4纸,手有些抖。深呼吸,将纸放入送纸器,按下电源键。
机器发出低沉的预热声,指示灯开始闪烁。我设定了十份复印,按下开始键。机器运作起来,
发出有节奏的、咔哒咔哒的声响。一张张白纸被吞入,又带着墨迹被吐出。
我紧紧盯着出纸口。第一张,干净。第二张,干净。……第五张,出来了。
我的呼吸骤然停止。在那张纸的右下角,一个清晰的、蜷缩着的孩童黑影印在那里!
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清晰,甚至能模糊分辨出头顶的发旋和抱膝的轮廓!它还在!
一股混杂着恐惧和“果然如此”的激动冲上头顶。我一把抓过那张纸,转身冲回办公区,
几乎是小跑着来到李姐的工位旁。“李姐!你看!就是这个!我没骗人!你看啊!
”我把那张纸几乎是戳到她眼前,声音因为激动而尖锐。李姐被我的举动吓了一跳,
扶了扶眼镜,接过纸张,对着光仔细看了半晌,又用手指抹了抹那个黑影。“小悦,
”她放下纸,表情是毫不掩饰的困惑和一丝不悦,“你到底想让我看什么?
这不就是一块墨粉污渍吗?可能是硒鼓老化或者漏粉了。这台机器确实该换换了。
”“不是污渍!是个人影!一个小孩!”我急得快哭出来。周围的同事被我的声音吸引,
纷纷投来目光。那些目光里有关切,有好奇,但更多的是疑惑和疏离。李姐叹了口气,
语气缓和下来,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定论:“小悦,你真的需要休息了。这样吧,
我给你放半天假,你现在就去医院看看,检查一下身体,好不好?工作上的事不用担心,
我让别人接手。”她的话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下。她不是在商量,而是在通知。
在她们眼里,我已经不是一个可靠的员工,而是一个需要被处理掉的“问题”。
没有人相信我。我拿着那张在我眼中清晰无比、在他人看来只是污渍的复印纸,僵在原地。
同事们的目光像细密的针,扎在我身上。就在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是幼儿园老师打来的。
一种更加不祥的预感瞬间攫住了我。我颤抖着接起电话。“喂?是林晓女士吗?
您能来幼儿园一趟吗?乐乐我儿子他……他有点不对劲。”“他怎么了?
”我的声音干涩。“他……他把班上所有的白色蜡笔都折断了,然后用黑色的蜡笔,
在所有的画纸上,反复涂鸦同一个奇怪的图案……我们问他画的是什么,
他说……”老师的声音带着迟疑和恐惧,“他说,是复印机里那个小朋友的脸。
他还说……那个小朋友,快要没有地方呆了。
”---3:理性的诊断与内心的裂隙我带着儿子乐乐从幼儿园回家,他的小手紧紧攥着我,
一路沉默。他折断了所有白色蜡笔,用黑色涂满了一张又一张纸,
那些扭曲的、被老师称为“脸”的黑色色块,此刻正躺在我的包里,像一块块灼热的炭。
李姐强制安排的“休假”成了事实。第二天,在丈夫他因紧急项目出差在外,
电话里语气担忧却遥远的催促和李姐隐晦的压力下,我预约了一位心理医生。
诊室温暖明亮,与外面阴沉的天气形成反差。周医生看起来很温和,四十多岁,
戴着金丝边眼镜,声音平稳得像一条没有波澜的河。
我艰难地复述了最近发生的一切:复印机上的人影,儿子的异常,警察和同事的不信任。
我甚至拿出了那张“有影子”的复印纸和乐乐画的“脸”。周医生仔细地听着,
看着那些“证据”,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问了许多问题:我的睡眠很差,多梦易醒,
饮食没胃口,工作压力很大,最近在竞标一个关键项目,以及家庭情况。“林女士,
据你所说,你的儿子乐乐是五岁。在他之前……你是否还有过其他孩子?
同类推荐
 执掌东宫:神医太子妃(林薇萧景玄)热门网络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执掌东宫:神医太子妃林薇萧景玄
执掌东宫:神医太子妃(林薇萧景玄)热门网络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执掌东宫:神医太子妃林薇萧景玄
朵朵小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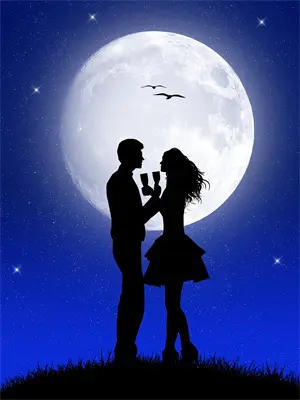 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最新好看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
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最新好看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
墨长哲
 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免费小说完整版_完结版小说阅读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
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免费小说完整版_完结版小说阅读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
墨长哲
 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免费小说完结版_最新章节列表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
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免费小说完结版_最新章节列表电竞:从游戏主播到全职GOAT(安君白王梓)
墨长哲
 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热门完结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
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热门完结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
梦曦一
 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免费小说完结版_最新章节列表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
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免费小说完结版_最新章节列表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
梦曦一
 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免费小说完结版_最新章节列表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
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免费小说完结版_最新章节列表快穿之情侣搭档惩治坏种之人(温栀棠顾衍)
梦曦一
 顾遥青灼华(世间都是命运棋)全章节在线阅读_(世间都是命运棋)完结版免费阅读
顾遥青灼华(世间都是命运棋)全章节在线阅读_(世间都是命运棋)完结版免费阅读
程晨之晨
 世间都是命运棋顾遥青灼华完结小说免费阅读_完本热门小说世间都是命运棋顾遥青灼华
世间都是命运棋顾遥青灼华完结小说免费阅读_完本热门小说世间都是命运棋顾遥青灼华
程晨之晨
 世间都是命运棋顾遥青灼华热门完结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世间都是命运棋(顾遥青灼华)
世间都是命运棋顾遥青灼华热门完结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世间都是命运棋(顾遥青灼华)
程晨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