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她弄脏了爱情,我擦干净了手(林晚靳砚)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她弄脏了爱情,我擦干净了手全文阅读
- 分类: 其它小说
- 作者:柿子和栗子
- 更新:2025-10-15 15:26:25
《她弄脏了爱情,我擦干净了手(林晚靳砚)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她弄脏了爱情,我擦干净了手全文阅读》精彩片段
结婚五周年纪念日,林晚说要去参加同学会。她回来时领口沾着陌生香水味,
锁骨下方有块新鲜红痕。我笑着递上热茶:“玩得开心吗?”她眼神躲闪:“就…叙叙旧。
”手机屏幕亮起,沈屿的短信跳出来:“晚晚,你落下的口红在我车上。”我捏碎了茶杯。
第一章靳砚把最后一道清蒸鲈鱼端上桌,细白瓷盘边沿还特意摆了两片翠绿的香菜叶。
餐厅顶灯的光晕温柔地洒下来,落在擦得锃亮的银质刀叉上,
也落在他无名指那圈素净的铂金戒环上,折射出一点微冷的星芒。桌中央,
冰桶里镇着一瓶年份不错的香槟,瓶身凝结的水珠正缓慢地滑落。墙上挂钟的指针,
不紧不慢地指向七点整。五周年纪念日,他记得清楚。玄关传来钥匙转动锁孔的轻响。
靳砚嘴角习惯性地弯起一个弧度,迎上去。门开了,林晚裹着一身室外的微凉空气进来,
脸颊带着运动后的红晕,眼睛亮得有些不寻常。她身上那件米白色羊绒衫的领口,
蹭上了一抹极淡的、近乎透明的粉金色痕迹,像某种昂贵香水的尾调。
靳砚的目光在那处停留了半秒,随即自然地落在她脸上。“回来了?”他接过她脱下的外套,
指尖不经意拂过她颈侧,那里皮肤温热。“嗯。”林晚应了一声,声音有点飘,低头换鞋,
浓密的睫毛垂下来,遮住了眼底的情绪,“路上有点堵。”“饿了吧?菜刚做好。
”靳砚把外套挂好,语气温和依旧,“先去洗洗手?”“好。”林晚匆匆应着,
几乎是逃也似的快步走向洗手间。靳砚站在原地,
鼻尖捕捉到一丝极其微弱、却异常顽固的香气。不是林晚惯用的那款清冷木质调,
而是一种更甜腻、更富有侵略性的花果香,带着点奶油杏仁的暖意,丝丝缕缕,
缠绕在刚才她领口那抹粉金色痕迹的位置。这香气很陌生,像一根细小的针,
无声无息地刺破了纪念日精心营造的温馨泡沫。他转身走向餐厅,脚步依旧平稳。
香槟瓶塞被熟练地旋开,发出“啵”的一声轻响,带着气泡的液体欢快地注入高脚杯。
林晚从洗手间出来,神色似乎镇定了一些,但眼神依旧有些飘忽,不敢与他对视。
她拉开椅子坐下,目光扫过满桌的菜,落在自己面前那杯冒着热气的红茶上。“怎么是茶?
”她随口问,拿起杯子抿了一口。“晚上喝香槟怕你胃不舒服。
”靳砚把一杯香槟推到她面前,自己拿起另一杯,金黄的液体在杯中轻轻晃动,
“不过纪念日,意思一下?”他举起杯,笑容温和,眼底却像沉静的深潭,
一丝波澜也无:“五周年快乐,晚晚。”林晚的手指蜷缩了一下,端起那杯香槟,杯壁冰凉。
她勉强扯出一个笑,声音有点干涩:“快乐。” 杯子轻轻碰了一下他的,
发出清脆的一声“叮”。她仰头喝了一大口,冰凉的液体滑过喉咙,
似乎让她紧绷的神经稍微松弛了一点。她放下杯子,拿起筷子,夹了一小块鲈鱼,
鱼肉雪白细嫩,是她喜欢的味道。她低头吃着,动作有些机械。靳砚也慢条斯理地吃着,
目光偶尔掠过她。餐厅里很安静,只有餐具偶尔碰撞的轻响。他注意到,
当她微微倾身去夹稍远一点的菜时,羊绒衫宽松的领口向下滑落了一点点,
在她左侧锁骨下方,靠近心脏的位置,一小块指甲盖大小的、边缘泛着新鲜红晕的痕迹,
毫无遮拦地暴露在灯光下。那不像磕碰,也不像过敏,更像是指尖用力揉捏后留下的印记。
那抹红痕,像一滴滚烫的蜡油,猝不及防地滴落在靳砚眼底。
他握着筷子的指节微微收紧了一下,随即又松开。脸上的笑容纹丝未动,甚至更温和了些。
他拿起公筷,夹了一块她爱吃的糖醋小排放进她碗里。“尝尝这个,今天火候应该刚好。
”林晚像是被惊了一下,猛地抬头看他,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慌乱,随即又强自镇定下来,
低声道:“谢谢。”“同学会…热闹吗?”靳砚状似随意地问,端起自己的香槟杯,
轻轻晃着,目光落在杯中细密上升的气泡上。林晚的筷子顿在半空,那块小排掉回了碗里。
她舔了舔有些发干的嘴唇,声音带着一种刻意的轻松:“嗯…还行吧,就那样。
好多年没见了,大家变化都挺大的。”“都聊了些什么?”靳砚追问,语气依旧温和,
像在聊天气。“还能聊什么呀,”林晚低下头,用筷子拨弄着碗里的米饭,
“无非就是工作、家庭、孩子…哦,还有以前上学时候的糗事,挺无聊的。
”她试图用“无聊”来淡化。“是吗?”靳砚轻轻抿了一口香槟,冰凉的液体滑入喉咙,
却压不住心底那簇骤然升起的、带着冰碴的火苗,“叙旧叙得开心就好。”“就…叙叙旧。
”林晚重复着,声音更低了,带着一种心虚的含糊。她端起茶杯,
想用热茶驱散那股莫名的心悸。就在这时,她放在桌角的手机屏幕,毫无预兆地亮了起来。
一条新信息的预览,像淬了毒的匕首,直直刺入靳砚的视线。发信人:沈屿。
内容预览:晚晚,你落下的口红在我车上,YSL那个方管,色号是…
后面几个字被屏幕边缘截断了,但那已经足够。“啪!”一声脆响,
突兀地打破了餐厅里虚假的宁静。靳砚手中那只薄如蝉翼的骨瓷茶杯,
被他无意识收紧的五指生生捏碎。滚烫的茶水混着几缕鲜红的血丝,
顺着他瞬间绷紧的手腕蜿蜒流下,滴落在洁白的桌布上,迅速洇开一小片刺目的红褐色污迹。
细小的瓷片深深扎进掌心,带来尖锐的痛感,
却奇异地压过了心头那股几乎要焚毁一切的暴怒。林晚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尖叫一声,
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噪音。她惊恐地看着靳砚流血的手,
又看看他脸上那瞬间褪去所有温和、只剩下一种近乎死寂冰冷的表情,嘴唇哆嗦着,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靳砚缓缓地、缓缓地抬起那只流血的手,
目光掠过掌心狰狞的伤口和嵌着的碎瓷,最终定格在林晚那张血色尽失、写满惊惶的脸上。
他扯动了一下嘴角,那笑容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眼底却像有黑色的风暴在无声地咆哮。
“手滑了。”他开口,声音低沉平稳,甚至带着一丝奇异的沙哑,却像冰锥一样扎人,
“看来这杯子,质量不太好。”第二章“靳砚!你的手!”林晚的声音因为惊恐而拔高,
带着尖锐的破音。她绕过桌子冲过来,想要抓住他流血的手腕查看。
靳砚却在她指尖即将触碰到自己的前一秒,猛地将手抽回,动作快得带起一阵风。
他看也没看自己血肉模糊的掌心,仿佛那只是无关紧要的擦伤。他的目光,
像两束冰冷的探照灯,牢牢锁在林晚脸上,
——难以置信的刺痛、被愚弄的暴怒、还有一丝连他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濒临失控的毁灭欲。
“别碰我。”他吐出三个字,声音不高,却像淬了冰的刀锋,瞬间冻住了林晚所有动作。
她僵在原地,伸出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指尖微微颤抖。餐厅顶灯的光线惨白地打在她脸上,
映出她眼中清晰的恐惧和心虚。她张了张嘴,想解释那条短信,
想解释领口的香水和锁骨下的红痕,但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发不出任何声音。
靳砚此刻的眼神太可怕了,那是一种她从未见过的、完全剥离了温情的审视,
让她感觉自己像被剥光了衣服钉在耻辱柱上。“我…我去拿药箱!”林晚终于找回一点声音,
带着哭腔,几乎是踉跄着转身冲向客厅的储物柜。她手忙脚乱地翻找着,
药箱里的瓶瓶罐罐被她碰得叮当作响。靳砚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温热的血顺着他的指尖滴落,在光洁的地板上砸开一小朵一小朵暗红的花。
掌心的剧痛清晰地传递到大脑,却奇异地带来一种近乎残忍的清醒。他低头,
看着那不断扩大的血渍,又抬眼,看向客厅里那个慌乱翻找的背影。那条短信,
像最精准的定位器,瞬间串联起所有可疑的碎片:她出门前精心挑选衣服时不同寻常的雀跃,
回来时领口陌生的甜腻香气,锁骨下新鲜的暧昧红痕,以及此刻她眼中无法掩饰的惊惶失措。
“叙旧?”他无声地咀嚼着这两个字,舌尖尝到一股浓重的铁锈味。原来所谓的同学会,
不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旧情复燃。沈屿。这个名字像一根毒刺,狠狠扎进他记忆深处。
林晚大学时的初恋,那个据说才华横溢、家境优渥的学长。原来这么多年,从未真正消失。
林晚终于找到了药箱,抱着它跌跌撞撞地跑回来,脸上挂着泪痕。“靳砚,快,让我看看!
得赶紧消毒包扎!”她声音发颤,带着哀求。靳砚没有动,只是冷冷地看着她。
那目光让林晚伸出的手再次僵住。“解释。”他开口,声音低沉得可怕,
每一个字都像冰雹砸落,“那条短信。沈屿。你落下的口红。”他顿了顿,
目光扫过她锁骨下方那抹刺眼的红,“还有这里。”林晚的脸瞬间褪尽最后一丝血色,
变得惨白如纸。她抱着药箱的手臂无力地垂下,药箱“哐当”一声掉在地上,
纱布和碘伏滚落出来。她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锁骨的位置,
仿佛这样就能遮住那昭然若揭的证据。“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徒劳地挣扎,
声音细若蚊蚋,眼神躲闪,
红可能是不小心掉他车上了…那个…那个是我不小心在洗手间磕到的…”她的解释苍白无力,
漏洞百出,连她自己都无法说服。“不小心?”靳砚重复着,嘴角勾起一个极其讽刺的弧度,
眼神却冷得能冻伤人,“在同学会的洗手间里,不小心磕到了锁骨下面?
还磕出了一个指印的形状?”他向前逼近一步,高大的身影带着强烈的压迫感,
将林晚完全笼罩在阴影里,“林晚,你是不是觉得我靳砚,是个彻头彻尾的傻子?
”“我没有!”林晚被他逼得后退一步,脊背撞在冰冷的餐边柜上,退无可退。
巨大的恐惧和谎言被戳穿的羞耻感让她浑身发抖,眼泪汹涌而出,“靳砚,你听我解释!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我和沈屿…我们只是…只是聊了聊…”“聊了聊?”靳砚打断她,
声音陡然拔高,带着压抑不住的戾气,在安静的餐厅里炸开,“聊到需要他送你回来?
聊到你的口红落在他车上?聊到你的身上沾满他的味道?聊到他在你身上留下这种印记?!
”他猛地指向她锁骨下的红痕,动作带起的风拂过林晚的脸颊,让她狠狠打了个寒颤。
“靳砚!”林晚崩溃地尖叫起来,双手捂住耳朵,身体顺着柜子滑坐到地上,蜷缩成一团,
泣不成声,
“对不起…对不起…我喝多了…我一时糊涂…真的只有那一次…我错了…求你…”“一次?
”靳砚居高临下地看着地上崩溃哭泣的女人,
这个他同床共枕五年、曾发誓要守护一生的妻子。她的眼泪,她的忏悔,此刻在他眼中,
只显得无比廉价和虚伪。心口那个被信任和爱意填满的地方,此刻被彻底掏空,
只剩下一个巨大的、呼呼灌着冷风的黑洞,以及从黑洞深处疯狂滋长蔓延的、冰冷的恨意。
他缓缓蹲下身,视线与瘫坐在地的林晚齐平。他伸出那只没有受伤的手,
动作甚至称得上轻柔,用指腹擦去她脸颊上滚烫的泪水。然而他的眼神,
却比西伯利亚的冻土还要寒冷坚硬。“晚晚,”他开口,声音异常平静,
平静得令人毛骨悚然,“你知道吗?信任这东西,就像这杯子。
”他瞥了一眼地上碎裂的骨瓷残片,“碎了,就再也拼不回去了。”他收回手,站起身,
不再看地上瑟瑟发抖的女人一眼。
他绕过地上的狼藉——碎裂的茶杯、滚落的药品、洇开的血渍和茶渍,径直走向厨房的水槽。
冰冷的水流冲刷着血肉模糊的掌心,刺痛尖锐,却让他混乱暴怒的大脑一点点冷却下来,
变得异常清晰、冷酷。他关掉水龙头,扯过一张厨房纸,随意地按在伤口上止血。
白色的纸巾迅速被染红。他转过身,背对着餐厅里压抑的哭泣声,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穿透空气,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凌:“收拾干净。然后,滚出我的视线。
”第三章主卧的门被靳砚从里面反锁,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像一道无形的闸门,
彻底隔绝了内外两个世界。门外,林晚压抑的、断断续续的啜泣声,隔着厚重的门板,
变得模糊而遥远,如同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噪音。靳砚背靠着冰冷的门板,缓缓滑坐在地毯上。
黑暗中,只有窗外城市遥远的光污染透进来一点微弱的、惨淡的光。他摊开那只受伤的手,
借着那点微光,看着掌心被水泡得发白、边缘依旧狰狞翻卷的伤口。血已经止住了,
但疼痛依旧清晰,一下下地敲打着他的神经。这痛,远不及心口那被彻底撕裂的万分之一。
沈屿。林晚。同学会。口红。香水。红痕。短信。这些词汇像淬毒的钢针,
反复穿刺着他脑海中名为“五年婚姻”的脆弱图景。每一次回想,
都让那幅图景碎裂得更加彻底,露出底下丑陋不堪的真相。他以为的安稳幸福,
不过是一场精心维持的骗局。他倾注了所有信任和温情的女人,在他精心准备纪念日的时候,
在另一个男人的车里,在另一个男人的身下……一股强烈的恶心感猛地涌上喉咙。
靳砚捂住嘴,干呕了几声,却什么也吐不出来,
只有冰冷的绝望和焚心的怒火在胸腔里疯狂冲撞。不行。不能这样。他猛地抬起头,黑暗中,
那双眼睛亮得惊人,像潜伏在丛林深处、被彻底激怒的猛兽。痛苦和悲伤被强行压下,
一种更冰冷、更坚硬、更危险的东西迅速占据了上风——那是被彻底背叛后,
从骨血里滋生出的、纯粹的恨意,以及一种近乎本能的、要撕碎一切的毁灭欲。他不能崩溃。
他不能像个懦夫一样沉溺在痛苦里。他要让背叛者付出代价。他要让沈屿,
那个自以为是的旧情人,彻底明白动了他靳砚的人,会是什么下场!他要让林晚,
亲眼看着她所珍视的一切,在她面前分崩离析!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像野火燎原,
瞬间吞噬了所有其他的情绪。一种奇异的、带着血腥味的兴奋感,开始沿着脊椎缓慢爬升。
靳砚撑着门板站起身,脚步有些虚浮,但眼神却锐利如刀。他走到书桌前,打开电脑。
屏幕的冷光映亮了他毫无血色的脸和紧抿的薄唇。他没有开灯,任由这唯一的光源将他笼罩。
他登录了一个极其隐秘的云端存储。里面存放着一些他从未想过会用到的东西——关于沈屿。
几年前,在一次偶然的商业合作接触中,靳砚凭借敏锐的直觉和谨慎的习惯,
曾对沈屿的背景和公司做过一次非正式的、极其深入的背调。当时只是出于商人的本能,
为了规避潜在风险。
上一些模糊不清的操作、几笔可疑的关联交易、以及他个人一些不太光彩的商场手段的资料,
被他随手加密存了起来,如同尘封的武器。现在,是时候让这些武器出鞘了。
他点开一个标注着“SY-财务疑点”的文件夹,
里面是扫描的票据、模糊的邮件截图、复杂的资金流向图。他看得极快,
大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运转着,筛选、分析、串联。沈屿的公司“屿帆科技”,表面光鲜,
主打智能家居,这两年融资势头不错,但根基并不稳,尤其财务方面,
为了维持估值和吸引下一轮投资,存在明显的……美化痕迹。
一些研发成本的资本化处理过于激进,几笔大额应收账款的真实性存疑,
甚至可能涉及虚增收入……靳砚的指尖在冰冷的键盘上快速敲击,
调出屿帆科技最新的公开财报和行业分析报告,与自己手中的“黑料”进行交叉比对。
屏幕的光在他眼中跳跃,映出一种近乎冷酷的专注。他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猎人,
在错综复杂的丛林里,精准地嗅到了猎物最致命的弱点。时间在死寂的黑暗中无声流逝。
窗外的城市灯火渐渐稀疏。靳砚忘记了掌心的疼痛,忘记了门外那个哭泣的女人,
甚至忘记了自己。他的全部心神,都沉浸在这场无声的狩猎前奏中。每一个可疑的数字,
每一条模糊的线索,都在他脑中逐渐清晰、放大,最终编织成一张足以致命的网。
当窗外天际泛起第一抹鱼肚白时,靳砚终于停下了敲击键盘的手指。他靠在椅背上,
长长地、无声地吐出一口浊气。一夜未眠,眼底布满血丝,但那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冷静。一个初步的、极具杀伤力的计划,在他脑中成型。不需要暴力,
不需要违法,只需要精准地找到那个支点,然后轻轻一撬。他要让沈屿引以为傲的事业,
他赖以生存的根基,在他最得意的时候,轰然倒塌!他要让林晚看看,她背叛自己选择的,
究竟是个什么样的货色!他拿起手机,屏幕的光照亮他毫无表情的脸。
他找到一个备注为“老K”的联系人。老K是他一个极其隐秘的线人,游走在灰色地带,
消息灵通,手段了得,最重要的是,只认钱,不问缘由。靳砚的手指在屏幕上敲击,
信息简洁冰冷:老K,屿帆科技,沈屿。我要他公司所有经不起查的账,尤其是近两年的。
还有他个人,所有能挖的黑料,越脏越好。钱不是问题,速度要快,痕迹要干净。
信息发送成功。他放下手机,目光投向窗外渐渐亮起的天空。晨曦微露,
却驱不散他眼底的阴霾,反而在那片冰冷中,点燃了一丝名为“复仇”的幽暗火焰。
客厅里传来极其轻微的脚步声,是林晚。她大概一夜未睡,此刻正小心翼翼地活动,
像一只惊弓之鸟。靳砚站起身,走到门边,没有开门,只是静静地站着,隔着门板,
听着外面那细微的、带着恐惧的动静。他嘴角缓缓勾起一个没有任何温度的弧度。游戏,
开始了。第四章接下来的日子,靳砚的公寓陷入一种诡异的平静,
如同暴风雨来临前令人窒息的死寂。靳砚手上的伤口结了痂,留下几道暗红色的丑陋疤痕。
他像往常一样上班、下班,甚至偶尔会和林晚在狭窄的玄关或客厅里擦肩而过。他不再看她,
不再和她说话,眼神掠过她时,如同掠过一件没有生命的家具,冰冷而漠然。他照常做饭,
但只做一人份。他依旧睡在主卧,门永远反锁。林晚则像生活在一个透明的牢笼里。
她试图道歉,试图解释,甚至在某天深夜鼓起勇气敲响了主卧的门,带着哭腔哀求:“靳砚,
我们谈谈好不好?求你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门内一片死寂,
没有任何回应。只有她自己的声音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显得格外凄凉和可笑。
她靠着门板滑坐在地,绝望像冰冷的潮水将她淹没。靳砚的沉默,
比任何暴怒的斥责都更让她恐惧。那是一种彻底的、不留余地的否定和驱逐。她开始失眠,
迅速消瘦下去,眼下的乌青浓得化不开,眼神总是惊惶不安,像一只随时会被惊飞的鸟。
她不敢出门,不敢联系沈屿,手机里沈屿发来的几条询问和安慰的信息,她一条也没敢回,
甚至不敢点开看。她被困在巨大的愧疚和恐惧中,等待着未知的审判。而靳砚,
则在这令人窒息的平静表象下,有条不紊地推动着他的计划。他成了一个完美的演员,
在公司,他依旧是那个冷静自持、能力出众的部门主管靳砚,处理着繁杂的事务,
参与着冗长的会议,甚至还能在茶水间和同事开两句无伤大雅的玩笑。
没有人能从他平静无波的外表下,窥见那汹涌的暗流。老K的效率很高。几天后,
一个加密的压缩包就悄无声息地躺在了靳砚指定的云端硬盘里。
超靳砚预期的“收获”:屿帆科技近两年核心的、经过“技术处理”的财务报表底稿扫描件,
清晰地显示着虚增收入、转移成本、伪造合同的痕迹;几份关键供应商和客户的秘密录音,
证实了串通做假账的事实;甚至还有沈屿私人邮箱里几封涉及内幕交易和贿赂的邮件截图,
虽然措辞隐晦,但指向性极其明确。更劲爆的是,
还有几段沈屿在不同场合与不同女人举止暧昧、甚至进入酒店房间的偷拍照片和视频。
这些资料,任何一项单独拎出来,都足以让沈屿和他的屿帆科技陷入巨大的麻烦。
而组合在一起,就是一枚足以将其彻底摧毁的核弹。靳砚花了整整一个晚上,
在绝对安全的网络环境下,仔细审阅了所有资料。他像一个最精密的仪器,
筛选出最具法律效力、最能一击致命的证据链,
同时剔除掉那些可能引火烧身的、过于灰色甚至黑色的部分。他要的是合法合规的毁灭,
而不是把自己也搭进去。证据整理完毕,他需要一个“安全”的投放渠道。
直接交给监管部门?太显眼,容易追查到自己。匿名举报?力度不够,容易被压下来。
他想到了一个人——赵哲。赵哲是他大学时代关系还算不错的同学,
毕业后进了本地一家以敢说真话、擅长挖掘财经黑幕而闻名的网络财经媒体,
如今已是副主编。最重要的是,赵哲欠他一个不小的人情,而且此人野心勃勃,
一直渴望做出轰动性的独家报道。靳砚用一张全新的、无法追踪来源的匿名电话卡,
拨通了赵哲的私人手机。“喂?哪位?”赵哲的声音带着被打扰的不耐。靳砚压低了嗓音,
用经过处理的、略带沙哑的电子音说道:“赵主编,
我手上有关于屿帆科技和沈屿的重磅黑料,足以让你登上头条,甚至拿奖。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赵哲的声音变得谨慎而充满兴趣:“你是谁?什么料?
”“我是谁不重要。”靳砚的声音冰冷而毫无起伏,“料绝对保真,虚增收入,财务造假,
关联交易输送利益,还有沈屿个人的‘精彩’生活。证据链完整,来源干净。
同类推荐
 我的竹马收藏簿(杜语倩林谌)完结版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我的竹马收藏簿杜语倩林谌
我的竹马收藏簿(杜语倩林谌)完结版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我的竹马收藏簿杜语倩林谌
玖日故事
 王逸司辰(我让富二代室友栽了)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王逸司辰全章节阅读
王逸司辰(我让富二代室友栽了)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王逸司辰全章节阅读
玖日故事
 重生归来,这次我不护着竹马了柳芊芊谢时渊免费小说_完本免费小说重生归来,这次我不护着竹马了柳芊芊谢时渊
重生归来,这次我不护着竹马了柳芊芊谢时渊免费小说_完本免费小说重生归来,这次我不护着竹马了柳芊芊谢时渊
玖日故事
 玥玥楚嫣温茶再遇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温茶再遇全本阅读
玥玥楚嫣温茶再遇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温茶再遇全本阅读
玖日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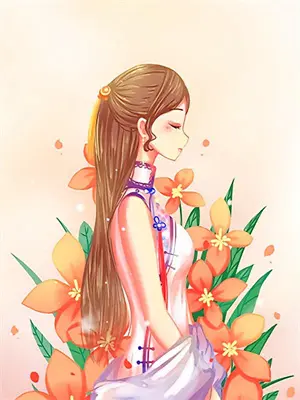 凭栏寄春山顾衍川林茵完本热门小说_小说推荐完结凭栏寄春山顾衍川林茵
凭栏寄春山顾衍川林茵完本热门小说_小说推荐完结凭栏寄春山顾衍川林茵
玖日故事
 夹在恋爱脑老板与控制狂女友间,我先溜了(林琦邱源)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夹在恋爱脑老板与控制狂女友间,我先溜了热门小说
夹在恋爱脑老板与控制狂女友间,我先溜了(林琦邱源)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夹在恋爱脑老板与控制狂女友间,我先溜了热门小说
玖日故事
 老婆嫁男闺蜜,我携大礼赴宴张浩宸孟绾绾最新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老婆嫁男闺蜜,我携大礼赴宴(张浩宸孟绾绾)
老婆嫁男闺蜜,我携大礼赴宴张浩宸孟绾绾最新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老婆嫁男闺蜜,我携大礼赴宴(张浩宸孟绾绾)
玖日故事
 《蜜桃熟于镜中花》米雪纪寻舟全集免费在线阅读_(米雪纪寻舟)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
《蜜桃熟于镜中花》米雪纪寻舟全集免费在线阅读_(米雪纪寻舟)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
玖日故事
 裴芳菲叶寒墨(裴芳菲叶寒墨)小说目录列表阅读-裴芳菲叶寒墨最新阅读
裴芳菲叶寒墨(裴芳菲叶寒墨)小说目录列表阅读-裴芳菲叶寒墨最新阅读
衍墨
 高速撒尿后,我成了连环杀手(李默李默)_李默李默热门小说
高速撒尿后,我成了连环杀手(李默李默)_李默李默热门小说
灼川无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