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换我人生?我回顶级豪门考状元》陈均罗大成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换我人生?我回顶级豪门考状元》全集阅读
- 分类: 都市小说
- 作者:南山松柏
- 更新:2025-10-12 03:33:19
《《换我人生?我回顶级豪门考状元》陈均罗大成全文免费在线阅读_《换我人生?我回顶级豪门考状元》全集阅读》精彩片段
我爸妈把迷药倒进我粥里时,我假装喝了。半夜骑了三十里山路到镇上派出所,
民警却笑着给我爸打电话:孩子闹脾气,你们来接一下。
第二天全村人都指着我说:王家丫头疯了,竟敢诬陷她爸妈下药。
直到那个北京来的陈老师按住我发抖的手:别怕,我带你报警。
查案时扯出三年前的高考顶替案,全县哗然。而手眼通天的生父家族找到我时,
我正对着镜头说:我要重考一次高考,拿回我的人生。
---爸妈把那种药拌进我的稀饭里时,我正低头数着碗里有几粒米。白色的粉末,
落在同样寡淡的稀饭里,其实看不太出来。就是他们盯着我的眼神,太烫了,像烧红的烙铁,
恨不得立刻在我身上打个记号。“招弟,快吃,吃完好睡觉,明天还得早起下地。
”妈把咸菜碟子往我面前推了推,声音是刻意放软的调子,听着别扭。我没吭声,端起碗,
借着仰头喝的动作,眼皮一掀,把那点不寻常看了个清清楚楚。碗沿碰着嘴唇,
稀饭根本没咽下去多少,大半都顺着袖口,偷偷淌进我预先垫在里面的旧布上。
心里冷得像三九天的冰窖。前几天夜里起来,我就听见他们的盘算了。
镇上的罗大成……愿意出这个数……就是得让丫头乖乖跟他走……”是我爸刻意压低的嗓音,
带着一种卖猪崽般的盘算。“她那个倔脾气……不用点法子……怎么弄?
”另一个魔鬼的声音响起,是我妈那尖酸刻薄的声音,“生她养她这么大,
也该为家里做点贡献了。”罗大成,镇上开赌档的,四十多了,一脸横肉,
前头那个老婆据说是跑没影的。原来,我就是那头待价而沽的猪崽。他们想用药送我上路。
碗底空了,我假装揉揉眼睛,打了个哈欠。“爸,妈,我困了,先去睡了。”“哎,好,
快去睡吧。”妈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放松。我躺在那张硬板床上,
睁眼看着糊满旧报纸的屋顶,耳朵竖得像雷达。等到隔壁传来沉重的鼾声,
等到窗外连狗叫都停了,我才悄没声地爬起来。心跳得像打鼓,手脚却稳得出奇。
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月光像冷水一样泼进来。我猫着腰,跑到屋后草垛子边,
推出那辆除了铃不响哪都响的破单车。骑上去,蹬起来,一头扎进黑漆漆的夜色里。
山路坑洼,夜风像刀子刮在脸上。我不敢停,拼命蹬着脚蹬子,链条发出哗啦啦的噪音,
在山谷里传得老远,惊起几声鸟叫。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去镇上,找派出所!三十里山路,
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骑下来的。到镇上天刚蒙蒙亮,街道冷清,只有早起的环卫工在扫地。
派出所的门开着,里面有个年轻民警正打着哈欠擦桌子。我冲进去,
不管头发被风吹得像草窝,还是衣服也被汗水跟露水打湿了,紧紧贴在身上。“叔叔,
我要报警!”我的嗓子干得冒烟,发出的声音嘶哑难听。那年轻民警吓了一跳,
看着我:“小姑娘,你怎么了?慢慢说。”“我爸我妈,他们昨晚给我下药!
想把我弄晕了卖给罗大成!”我一口气说出来,胸口剧烈起伏。民警愣了一下,
眉头皱起来:“下药?卖人?你说你爸妈?”他上下打量我,眼神里是毫不掩饰的怀疑,
“小姑娘,你是不是跟家里闹矛盾,吵架跑出来的?”“不是!是真的!
我亲眼看见他们把药粉拌在我饭里!我假装喝了……”我急得往前凑,
想让他看清我眼里的惊恐。民警却往后仰了仰,
脸上露出一种“又来了个不省心孩子”的表情。他拿起桌上的座机话筒,
一边拨号一边说:“行了行了,别闹了,哪个村的?我给你家打电话,让你爸妈来接你。
”我如坠冰窟。“别!不能打!”可他已经在问了:“喂,是王家村的王老四家吗?
你家是不是有个姑娘……”我瘫坐在冰凉的长椅上,
听着他跟电话那头我爸赔着笑说“孩子闹脾气”“快来接回去吧”,浑身的力量都被抽干了。
完了。我爸来得飞快,骑着他那辆摩托,脸上堆着讨好的笑,一进门就塞给那民警一根烟。
“对不住啊同志,丫头不懂事,跟我们置气呢,瞎胡说,给您添麻烦了!
”民警摆摆手:“没事,带孩子回去好好说,别打骂。”爸一把攥住我的胳膊,手指像铁钳,
脸上在笑,眼神却阴狠。“走,跟爸回家!”我被他死死拖着,拽出了派出所。门口,
罗大成那辆黑色的桑塔纳就停在那里,他摇下车窗,嘴里叼着烟,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那眼神,像毒蛇的信子舔过我的皮肤。我爸把我往车后座一塞,砰地关上门。
罗大成发动车子,慢悠悠地说:“老四,你这闺女,性子挺烈啊。”我爸坐在副驾,
扭头瞪我:“回去好好收拾你!”我没看他,只是死死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道,
指甲掐进了掌心。车子没开回村,直接停在了罗大成镇上的房子门口。他拽着我下车,
把我往屋里推。“进了这个门,就给我老实点!”罗大成露出狰狞的本相。我瞅准一个空档,
猛地挣脱他,转身就往街上跑!脑子里只有一个名字——陈老师!那个从北京来的,
在镇中学代过课的陈老师!罗大成有一次看到陈老师,那点头哈腰的样子,我记得!
“臭丫头!站住!”罗大成在后面追。我拼命跑,肺像要炸开。拐过街角,
一眼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正从一家早点铺子出来。“陈老师!”我尖叫着扑过去,
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整个人抖得像风里的落叶。陈均被撞得一个趔趄,看清是我,愣了一下,
随即扶住我:“王招弟?你怎么……”话没说完,罗大成已经追到了跟前,喘着粗气,
脸上横肉抖动,但看到陈均,气势瞬间矮了半截,挤出一个难看的笑:“陈、陈老师,
这……这我家不听话的丫头,我这就带她回去。”陈均没松手,
他看看面无人色、抖个不停的我,又看看一脸凶相、明显不对劲的罗大成,眉头慢慢拧紧。
“罗老板,”陈均的声音很平静,却有种不容置疑的力量,“这姑娘好像很害怕。有什么事,
就在这里说清楚吧。”“没啥事!就是家务事!”罗大成急着想拉我。
我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死死抱住陈均的胳膊,
语无伦次地喊出来:“他跟我爸妈合伙给我下药!要卖我!陈老师,救救我!我去报警了,
可派出所不信我!”陈均的脸色瞬间沉了下去。他把我往身后一带,
完全挡在我和罗大成之间,目光锐利地看向罗大成:“下药?买卖人口?罗老板,这是犯罪。
”罗大成脸都白了,支吾着:“她、她胡说八道!陈老师,
您别听她瞎说……”“是不是瞎说,让警察调查清楚再说。”陈均不再看他,直接拿出手机,
拨了个号码,语气不容置疑,“喂,李局吗?我陈均,镇上可能有个案子,
涉及到非法拘禁和人口买卖,对,我现在就在现场……”罗大成听到“李局”两个字,
腿都软了,汗珠子顺着额头往下滚,再不敢上前。这一次,不一样了。警车呜哇呜哇地来了,
来的不是那个年轻民警,而是几个神色严肃的警察,直接就把面如死灰的罗大成带走了。
我也被带回去重新做笔录,陈老师一直陪着我。案子顺着罗大成这根藤,
摸到了我爸妈那个瓜。审讯室里,我妈先扛不住,哭嚎着把事都说了,
连同埋怨一起:“我们有什么办法!谁让她个死丫头片子不肯听话!再说,
当年四婶家叶儿顶了她上大学的事,我们不也认了嘛!都是闺女,谁去上不是上!
”做笔录的警察笔尖一顿,猛地抬头。一石激起千层浪。三年前我高考“落榜”,
村里谁都可惜了一阵,说我念书那么灵光,可惜了。原来不是可惜,是特么我的录取通知书,
早就被我妈用两千块钱加上“都是亲戚”的人情,卖给了四婶家的女儿陆叶儿了!
王叶儿现在人在北京,上读了一年大学了!消息传开,全县哗然。我爸我妈,还有我四婶,
全都进了局子。顶替上大学的陆叶儿,也被学校取消了学籍,从北京灰溜溜地回来了。
事情闹得很大,报纸电视都报了。就在这乱糟糟的时候,陈老师找到了我,眼神有些复杂。
“招弟,你之前……是不是暗示过我,你可能不是王老四亲生的?”我抬起头,看着他。
这事我一直有模糊的印象,小时候听村里老人嚼过舌根,说我可能是被扔在村口的,
脖颈后面有块小疤痕,像是什么信物。我偷偷跟陈老师提过一次。
陈老师叹了口气:“北京那边,有个陆家,一直在找很多年前丢失的一个小女孩,
特征……跟你很像。他们看到新闻了,联系了我。”我跟着陈老师上了北京。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那么高的楼,那么宽的路,那么多飞驰的汽车。陆家,
同类推荐
 我捐肾救兄,他们骂我捐晚了晓晓李强免费小说完整版_热门的小说我捐肾救兄,他们骂我捐晚了晓晓李强
我捐肾救兄,他们骂我捐晚了晓晓李强免费小说完整版_热门的小说我捐肾救兄,他们骂我捐晚了晓晓李强
李可妮
 说好的点石成金,点出个债主怎么办(刀疤金子)全集阅读_说好的点石成金,点出个债主怎么办最新章节阅读
说好的点石成金,点出个债主怎么办(刀疤金子)全集阅读_说好的点石成金,点出个债主怎么办最新章节阅读
十三狮子
 我,一个平平无奇的女大学生,把禁欲教授拉下神坛(林溪陆之珩)全本完结小说_完整版免费全文阅读我,一个平平无奇的女大学生,把禁欲教授拉下神坛(林溪陆之珩)
我,一个平平无奇的女大学生,把禁欲教授拉下神坛(林溪陆之珩)全本完结小说_完整版免费全文阅读我,一个平平无奇的女大学生,把禁欲教授拉下神坛(林溪陆之珩)
tianking
 《重生归来,我把渣男虐到跪地求饶》(陈宇林悦)完本小说_热门的小说《重生归来,我把渣男虐到跪地求饶》陈宇林悦
《重生归来,我把渣男虐到跪地求饶》(陈宇林悦)完本小说_热门的小说《重生归来,我把渣男虐到跪地求饶》陈宇林悦
出水芙蓉的水仙
 痛感转移我受的痛,全让欺负我的人扛苏卿卿萧彻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好看小说痛感转移我受的痛,全让欺负我的人扛苏卿卿萧彻
痛感转移我受的痛,全让欺负我的人扛苏卿卿萧彻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好看小说痛感转移我受的痛,全让欺负我的人扛苏卿卿萧彻
没怎么办要输了
 前夫葬礼,他的白月光哭着求我复婚(陆宴臣傅明州)完本小说_热门的小说前夫葬礼,他的白月光哭着求我复婚陆宴臣傅明州
前夫葬礼,他的白月光哭着求我复婚(陆宴臣傅明州)完本小说_热门的小说前夫葬礼,他的白月光哭着求我复婚陆宴臣傅明州
大王月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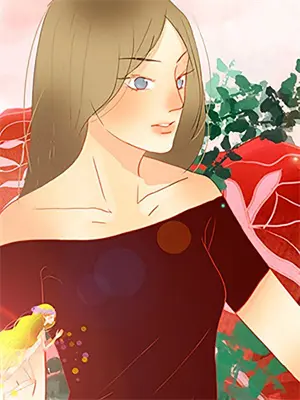 程子墨,吸烟喝酒,你可是样样都会呀!(恭耀青程子墨)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_完结小说程子墨,吸烟喝酒,你可是样样都会呀!恭耀青程子墨
程子墨,吸烟喝酒,你可是样样都会呀!(恭耀青程子墨)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_完结小说程子墨,吸烟喝酒,你可是样样都会呀!恭耀青程子墨
超安静的风
 我替姐姐冲喜,京圈太子爷却只碰我。姜月瑶谢泽推荐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我替姐姐冲喜,京圈太子爷却只碰我。(姜月瑶谢泽)
我替姐姐冲喜,京圈太子爷却只碰我。姜月瑶谢泽推荐完结小说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我替姐姐冲喜,京圈太子爷却只碰我。(姜月瑶谢泽)
我是饼干
 我捧红了她,她却给了我封杀令秦宇苏晚最新好看小说_最新完本小说我捧红了她,她却给了我封杀令秦宇苏晚
我捧红了她,她却给了我封杀令秦宇苏晚最新好看小说_最新完本小说我捧红了她,她却给了我封杀令秦宇苏晚
李可妮
 我的巨婴闺蜜(王佳佳王佳佳)免费小说阅读_完结版小说推荐我的巨婴闺蜜(王佳佳王佳佳)
我的巨婴闺蜜(王佳佳王佳佳)免费小说阅读_完结版小说推荐我的巨婴闺蜜(王佳佳王佳佳)
熬猪油的白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