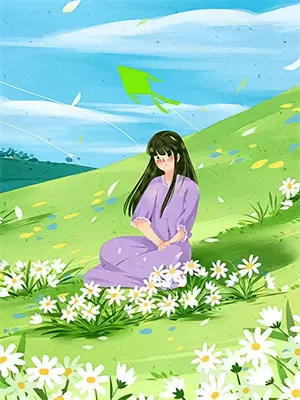- 《仙劫缘》赵勤赵芸完结版阅读_赵勤赵芸完结版在线阅读
- 分类: 奇幻玄幻
- 作者:怀飞
- 更新:2025-09-30 16:57:08
阅读全本
小说叫做《仙劫缘》,是作者怀飞的小说,主角为赵勤赵芸。本书精彩片段:东汉末年,龙气崩散,灵衰之劫蔓延。三国烽火不独燃于人间,更延烧至修仙界。 赵勤,字子瞻,蜀汉一普通士卒,曾见五虎上将之勇,亦尝乱世蝼蚁之悲。一场死劫,他坠入深渊,却得遇神秘南华老仙,就此踏上凶险莫测的修仙之路。 前有战场修罗劫,后有宗门暗算刀。从旁门散修到蜀山弟子,从炼气蝼蚁到化神剑仙。赵勤凭借一颗坚毅道心,于仙魔倾轧的夹缝中,寻得一线长生之机。 当他执剑问天,脚下已是魏蜀吴三国龙脉交织的棋局。这乱世,究竟是天命的终结,还是仙途的起点?
加之天灾连年,疫病横行,苛捐杂税猛于虎狼,神州大地早己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偌大一个汉家天下,仿佛一架千疮百孔的破旧马车,正沿着陡峭的山崖,一路呼啸着奔向那万劫不复的深渊。
蜀地自古号称天府之国,有岷江、涪江滋养,沃野千里,本是乱世中难得的避祸之所。
然而,在这灵帝熹平年间,即便是相对安稳的梓潼郡内,也早己弥漫起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息。
郡县之间,道路两旁,时见拖家带口、面有菜色的流民,如同无根的浮萍,漫无目的地漂泊,只为寻一口活命的吃食。
梓潼郡下属有一个名为“赵家集”的小小村落,聚着几十户人家,大多姓赵,依着一条名为“清衣江”的支流而建。
村中房屋多是黄土垒墙,茅草覆顶,低矮而破败。
时近黄昏,夕阳的余晖给这片贫瘠的土地涂抹上了一层凄凉的橘红色,几缕稀稀拉拉的炊烟升起,更添几分暮色苍茫。
在村子最西头,靠近一片乱葬岗的角落,有一间尤其残破的土屋。
屋角的茅草己被雨水烂穿了大半,墙壁上也裂开了几道狰狞的口子,用混着干草的泥巴勉强糊住。
此刻,一个瘦小的身影正蹲在屋前一块磨刀石前,专注地磨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柴刀。
这少年看上去约莫十岁光景,身形单薄得如同秋风中的芦苇杆,仿佛一阵稍大些的风就能将他吹倒。
他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打满补丁的粗麻布短褂,下身是一条几乎褪成灰白色的裤子,膝盖处磨得快要透光。
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他的面色泛着一种不健康的蜡黄,头发也显得有些枯黄稀疏,用一根草绳胡乱扎在脑后。
然而,若有人此刻能走近细看,便会发现这少年与其他村童截然不同之处。
他那张尚带稚气的脸上,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那不是孩童天真烂漫的光芒,而是一种过早承受生活重压后,磨砺出的沉静与坚韧。
他的眼神异常专注,紧盯着柴刀的刃口,双手稳定地前后推动,发出“沙沙”的声响,每一次摩擦都精准而有力。
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却恍若未觉,只是偶尔抬起手臂,用那破旧的袖子胡乱擦一下。
这少年,便是赵勤,字子瞻。
名字是他那读过几年蒙学、却屡试不第的父亲赵老汉,在欣喜之余,翻烂了一本残破的《论语》后给取的。
“勤”字望其能勤勉立身,“子瞻”则取自“登轼而望之”,隐约寄托了父亲希望儿子能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眼界高远的微末期盼。
只是在这等年月,温饱尚且难求,这般期望,未免显得太过奢侈了些。
赵勤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六岁的妹妹赵芸和一个尚在蹒跚学步的弟弟赵俭。
母亲体弱多病,一家五口的生计,几乎全压在了父亲赵老汉那早己被岁月和劳苦压弯的脊梁上。
赵老汉除了耕种那几亩贫瘠的租田,闲暇时便去清衣江上帮人撑船,或是进山砍些柴火贩卖,换回些许微薄的铜钱,勉强维持着这个家不至于散掉。
“哥,哥……我饿……”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赵勤停下手中的动作,转过头,看见妹妹赵芸扶着门框,探出半个小脑袋,一双大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小手不自觉地揉着干瘪的肚子。
赵勤心中一酸,脸上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放下柴刀站起身,走到妹妹身边,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芸娘乖,再忍一忍,爹就快回来了,等爹回来就有吃的了。”
他的声音还带着孩童的清脆,但语气里却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沉稳。
他知道,家里的米缸早己见了底,母亲昨日便只喝了些野菜糊糊,今日父亲一早进山,说是去碰碰运气,看能否采到些值钱的草药,或者打到只山鸡野兔。
能否有收获,全看天意。
安抚好妹妹,赵勤重新蹲下,更加用力地磨起柴刀。
他必须在天彻底黑透之前,把刀磨得锋利些,明天一早,他计划着去村后那座据说有野狼出没的矮山碰碰运气。
虽然危险,但若能砍到足够的柴火,或者侥幸设套捉到只野兔,至少能让母亲和弟妹吃上一顿稍微像样的饭食。
作为长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分担父亲的重担。
这种远超年龄的责任感,并非凭空而来。
赵勤的童年,几乎是在颠沛流离和死亡的阴影中度过的。
他依稀记得,大约在西五岁时,郡里闹过一场极大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过后,田地颗粒无收。
那时,父亲也曾带着他们一家,加入过那望不到头的流民队伍,一路乞讨,挣扎求存。
他亲眼见过饿殍倒毙路旁,无人收殓;亲眼见过为了一块发霉的饼子,平日里和善的乡邻可以打得头破血流;更亲眼见过母亲为了省下一口吃的给他和妹妹,自己饿得昏厥过去。
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如同烧红的烙铁,深深印在了他幼小的心灵上。
让他早早明白了生活的残酷,也让他懂得了“活下去”这三个字,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他沉默寡言,并非天性如此,而是深知在这乱世,多余的言语和情绪都是奢侈,唯有行动和坚韧,才是生存的根本。
他也曾羡慕过村里那寥寥几个能去邻村老秀才家识字的孩童,但他从未向父母提起过。
他知道,那每年几斗米的束脩,对这个家庭来说,是无法承受的重负。
他只能偶尔在帮父亲去镇上送柴时,偷偷趴在学堂的窗口,听里面传来几句“之乎者也”的诵读声,心中暗自记下。
父亲那本残破的《论语》,便是他识字的唯一启蒙,虽大多不解其意,却也能磕磕绊绊念上几句。
“勤娃子!”
一声带着疲惫却又隐含一丝兴奋的呼唤,从村口方向传来。
赵勤猛地抬头,只见父亲赵老汉的身影正沿着土路快步走来。
父亲的身形依旧佝偻,肩上扛着一捆柴火,手里似乎还提着什么东西。
赵勤立刻站起身,迎了上去。
走近了才看清,父亲手里提着的,是一只肥硕的野兔,还有几株沾着泥土的草药。
“爹!”
赵勤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欣喜。
赵老汉将柴火放下,把野兔和草药递给赵勤,蜡黄的脸上难得地有了一丝笑意:“今天运气不赖,这畜生撞到俺下的套子了。
这几株‘血见愁’,镇上的药铺应该能换几个钱。”
赵勤接过沉甸甸的野兔,心中一块大石落地,今晚,家人终于可以吃上一顿肉了。
他小心地接过那几株草药,他知道,这叫“血见愁”的草药能止血,是刀伤药的主要成分,对时常受伤的穷苦人家和军中都很紧俏,确实能换些粮食。
父子二人回到那间破旧的土屋。
母亲挣扎着从炕上起来,看到野兔,灰暗的脸上也焕发出一丝光彩,连忙接过,和赵芸一起张罗着收拾起来。
小小的弟弟赵俭咿咿呀呀地围着母亲转悠,屋内难得地有了一丝温馨的气息。
晚饭是难得一见的野菜炖兔肉,虽然盐放得极少,但对于常年不见荤腥的一家人来说,己是无上的美味。
赵勤默默地吃着,将大部分肉块都夹给了母亲和弟妹,自己只挑些骨头和野菜。
父亲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既有欣慰,也有深深的内疚。
饭后,母亲带着弟妹早早睡下。
赵勤和父亲坐在屋外的石墩上,就着微弱的月光,整理着明天的柴火和草药。
“勤娃子,”赵老汉沉默半晌,忽然压低声音道,“今天在山里,俺听到几个从北面逃难过来的人说,北边……越来越不太平了,估计要打仗,怕是……要出大事啊。”
赵勤手中动作一顿,抬起头,看着父亲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忧虑的侧脸。
他虽然年幼,但也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和流民惶恐的神情中,模糊地感觉到,这世道,恐怕真的要彻底大乱了。
村正前些日子还来催缴了明年的赋税,说是郡守大人有令,要加固城防,以备不测。
“爹,不管出啥事,咱一家人在一起,总有办法。”
赵勤轻声说道,语气坚定。
赵老汉看着儿子那双在夜色中依然清亮的眼睛,心中百感交集,最终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睡吧,明天还得早起。”
是夜,赵勤躺在冰冷的土炕上,听着身旁弟妹均匀的呼吸声,以及窗外呜咽而过的夜风,久久无法入睡。
他想起父亲的话,想起流民绝望的眼神,想起村正催税时凶狠的嘴脸。
一种对未来的茫然和隐隐的不安,如同冰冷的毒蛇,缠绕上他的心间。
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传来细微的刺痛感。
这吃人的世道,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丝光亮吗?
少年不知,命运的轨迹,往往就在这最深的黑暗处悄然转折。
十数年后的那场坠崖,那场看似绝境的死劫,将会为他,也为这个即将彻底崩坏的世界,带来一场谁也预料不到的惊天变数。
而此刻,他只是一个在乱世尘埃中,挣扎求存的寒门之子,赵勤,赵子瞻。
《《仙劫缘》赵勤赵芸完结版阅读_赵勤赵芸完结版在线阅读》精彩片段
时值东汉末年,桓灵昏聩,宦官外戚交替专权,朝纲败坏如朽木。加之天灾连年,疫病横行,苛捐杂税猛于虎狼,神州大地早己是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偌大一个汉家天下,仿佛一架千疮百孔的破旧马车,正沿着陡峭的山崖,一路呼啸着奔向那万劫不复的深渊。
蜀地自古号称天府之国,有岷江、涪江滋养,沃野千里,本是乱世中难得的避祸之所。
然而,在这灵帝熹平年间,即便是相对安稳的梓潼郡内,也早己弥漫起一股山雨欲来的压抑气息。
郡县之间,道路两旁,时见拖家带口、面有菜色的流民,如同无根的浮萍,漫无目的地漂泊,只为寻一口活命的吃食。
梓潼郡下属有一个名为“赵家集”的小小村落,聚着几十户人家,大多姓赵,依着一条名为“清衣江”的支流而建。
村中房屋多是黄土垒墙,茅草覆顶,低矮而破败。
时近黄昏,夕阳的余晖给这片贫瘠的土地涂抹上了一层凄凉的橘红色,几缕稀稀拉拉的炊烟升起,更添几分暮色苍茫。
在村子最西头,靠近一片乱葬岗的角落,有一间尤其残破的土屋。
屋角的茅草己被雨水烂穿了大半,墙壁上也裂开了几道狰狞的口子,用混着干草的泥巴勉强糊住。
此刻,一个瘦小的身影正蹲在屋前一块磨刀石前,专注地磨着一把锈迹斑斑的柴刀。
这少年看上去约莫十岁光景,身形单薄得如同秋风中的芦苇杆,仿佛一阵稍大些的风就能将他吹倒。
他穿着一件明显不合身的、打满补丁的粗麻布短褂,下身是一条几乎褪成灰白色的裤子,膝盖处磨得快要透光。
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他的面色泛着一种不健康的蜡黄,头发也显得有些枯黄稀疏,用一根草绳胡乱扎在脑后。
然而,若有人此刻能走近细看,便会发现这少年与其他村童截然不同之处。
他那张尚带稚气的脸上,一双眼睛却亮得惊人。
那不是孩童天真烂漫的光芒,而是一种过早承受生活重压后,磨砺出的沉静与坚韧。
他的眼神异常专注,紧盯着柴刀的刃口,双手稳定地前后推动,发出“沙沙”的声响,每一次摩擦都精准而有力。
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他却恍若未觉,只是偶尔抬起手臂,用那破旧的袖子胡乱擦一下。
这少年,便是赵勤,字子瞻。
名字是他那读过几年蒙学、却屡试不第的父亲赵老汉,在欣喜之余,翻烂了一本残破的《论语》后给取的。
“勤”字望其能勤勉立身,“子瞻”则取自“登轼而望之”,隐约寄托了父亲希望儿子能有朝一日出人头地、眼界高远的微末期盼。
只是在这等年月,温饱尚且难求,这般期望,未免显得太过奢侈了些。
赵勤是家中长子,下面还有一个六岁的妹妹赵芸和一个尚在蹒跚学步的弟弟赵俭。
母亲体弱多病,一家五口的生计,几乎全压在了父亲赵老汉那早己被岁月和劳苦压弯的脊梁上。
赵老汉除了耕种那几亩贫瘠的租田,闲暇时便去清衣江上帮人撑船,或是进山砍些柴火贩卖,换回些许微薄的铜钱,勉强维持着这个家不至于散掉。
“哥,哥……我饿……”一个怯生生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赵勤停下手中的动作,转过头,看见妹妹赵芸扶着门框,探出半个小脑袋,一双大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小手不自觉地揉着干瘪的肚子。
赵勤心中一酸,脸上却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放下柴刀站起身,走到妹妹身边,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芸娘乖,再忍一忍,爹就快回来了,等爹回来就有吃的了。”
他的声音还带着孩童的清脆,但语气里却有一种超乎年龄的沉稳。
他知道,家里的米缸早己见了底,母亲昨日便只喝了些野菜糊糊,今日父亲一早进山,说是去碰碰运气,看能否采到些值钱的草药,或者打到只山鸡野兔。
能否有收获,全看天意。
安抚好妹妹,赵勤重新蹲下,更加用力地磨起柴刀。
他必须在天彻底黑透之前,把刀磨得锋利些,明天一早,他计划着去村后那座据说有野狼出没的矮山碰碰运气。
虽然危险,但若能砍到足够的柴火,或者侥幸设套捉到只野兔,至少能让母亲和弟妹吃上一顿稍微像样的饭食。
作为长子,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分担父亲的重担。
这种远超年龄的责任感,并非凭空而来。
赵勤的童年,几乎是在颠沛流离和死亡的阴影中度过的。
他依稀记得,大约在西五岁时,郡里闹过一场极大的蝗灾,遮天蔽日的蝗虫过后,田地颗粒无收。
那时,父亲也曾带着他们一家,加入过那望不到头的流民队伍,一路乞讨,挣扎求存。
他亲眼见过饿殍倒毙路旁,无人收殓;亲眼见过为了一块发霉的饼子,平日里和善的乡邻可以打得头破血流;更亲眼见过母亲为了省下一口吃的给他和妹妹,自己饿得昏厥过去。
那些刻骨铭心的记忆,如同烧红的烙铁,深深印在了他幼小的心灵上。
让他早早明白了生活的残酷,也让他懂得了“活下去”这三个字,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他沉默寡言,并非天性如此,而是深知在这乱世,多余的言语和情绪都是奢侈,唯有行动和坚韧,才是生存的根本。
他也曾羡慕过村里那寥寥几个能去邻村老秀才家识字的孩童,但他从未向父母提起过。
他知道,那每年几斗米的束脩,对这个家庭来说,是无法承受的重负。
他只能偶尔在帮父亲去镇上送柴时,偷偷趴在学堂的窗口,听里面传来几句“之乎者也”的诵读声,心中暗自记下。
父亲那本残破的《论语》,便是他识字的唯一启蒙,虽大多不解其意,却也能磕磕绊绊念上几句。
“勤娃子!”
一声带着疲惫却又隐含一丝兴奋的呼唤,从村口方向传来。
赵勤猛地抬头,只见父亲赵老汉的身影正沿着土路快步走来。
父亲的身形依旧佝偻,肩上扛着一捆柴火,手里似乎还提着什么东西。
赵勤立刻站起身,迎了上去。
走近了才看清,父亲手里提着的,是一只肥硕的野兔,还有几株沾着泥土的草药。
“爹!”
赵勤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属于他这个年龄的欣喜。
赵老汉将柴火放下,把野兔和草药递给赵勤,蜡黄的脸上难得地有了一丝笑意:“今天运气不赖,这畜生撞到俺下的套子了。
这几株‘血见愁’,镇上的药铺应该能换几个钱。”
赵勤接过沉甸甸的野兔,心中一块大石落地,今晚,家人终于可以吃上一顿肉了。
他小心地接过那几株草药,他知道,这叫“血见愁”的草药能止血,是刀伤药的主要成分,对时常受伤的穷苦人家和军中都很紧俏,确实能换些粮食。
父子二人回到那间破旧的土屋。
母亲挣扎着从炕上起来,看到野兔,灰暗的脸上也焕发出一丝光彩,连忙接过,和赵芸一起张罗着收拾起来。
小小的弟弟赵俭咿咿呀呀地围着母亲转悠,屋内难得地有了一丝温馨的气息。
晚饭是难得一见的野菜炖兔肉,虽然盐放得极少,但对于常年不见荤腥的一家人来说,己是无上的美味。
赵勤默默地吃着,将大部分肉块都夹给了母亲和弟妹,自己只挑些骨头和野菜。
父亲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既有欣慰,也有深深的内疚。
饭后,母亲带着弟妹早早睡下。
赵勤和父亲坐在屋外的石墩上,就着微弱的月光,整理着明天的柴火和草药。
“勤娃子,”赵老汉沉默半晌,忽然压低声音道,“今天在山里,俺听到几个从北面逃难过来的人说,北边……越来越不太平了,估计要打仗,怕是……要出大事啊。”
赵勤手中动作一顿,抬起头,看着父亲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忧虑的侧脸。
他虽然年幼,但也从大人们的只言片语和流民惶恐的神情中,模糊地感觉到,这世道,恐怕真的要彻底大乱了。
村正前些日子还来催缴了明年的赋税,说是郡守大人有令,要加固城防,以备不测。
“爹,不管出啥事,咱一家人在一起,总有办法。”
赵勤轻声说道,语气坚定。
赵老汉看着儿子那双在夜色中依然清亮的眼睛,心中百感交集,最终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拍了拍儿子的肩膀:“睡吧,明天还得早起。”
是夜,赵勤躺在冰冷的土炕上,听着身旁弟妹均匀的呼吸声,以及窗外呜咽而过的夜风,久久无法入睡。
他想起父亲的话,想起流民绝望的眼神,想起村正催税时凶狠的嘴脸。
一种对未来的茫然和隐隐的不安,如同冰冷的毒蛇,缠绕上他的心间。
他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传来细微的刺痛感。
这吃人的世道,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丝光亮吗?
少年不知,命运的轨迹,往往就在这最深的黑暗处悄然转折。
十数年后的那场坠崖,那场看似绝境的死劫,将会为他,也为这个即将彻底崩坏的世界,带来一场谁也预料不到的惊天变数。
而此刻,他只是一个在乱世尘埃中,挣扎求存的寒门之子,赵勤,赵子瞻。
同类推荐
 阵阵酒儿香(陆酒铁柱)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陆酒铁柱全文阅读
阵阵酒儿香(陆酒铁柱)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陆酒铁柱全文阅读
歇脚的风
 阵阵酒儿香陆酒铁柱免费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阵阵酒儿香(陆酒铁柱)
阵阵酒儿香陆酒铁柱免费小说全文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阵阵酒儿香(陆酒铁柱)
歇脚的风
 阵阵酒儿香陆酒铁柱免费小说大全_小说完结阵阵酒儿香(陆酒铁柱)
阵阵酒儿香陆酒铁柱免费小说大全_小说完结阵阵酒儿香(陆酒铁柱)
歇脚的风
 我,红旗下的凶兽(阿波罗张燎)完整版免费阅读_(我,红旗下的凶兽)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
我,红旗下的凶兽(阿波罗张燎)完整版免费阅读_(我,红旗下的凶兽)全章节免费在线阅读
梦好莫催醒
 我,红旗下的凶兽阿波罗张燎完整版免费小说_热门网络小说推荐我,红旗下的凶兽(阿波罗张燎)
我,红旗下的凶兽阿波罗张燎完整版免费小说_热门网络小说推荐我,红旗下的凶兽(阿波罗张燎)
梦好莫催醒
 我,红旗下的凶兽阿波罗张燎完本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免费阅读我,红旗下的凶兽(阿波罗张燎)
我,红旗下的凶兽阿波罗张燎完本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免费阅读我,红旗下的凶兽(阿波罗张燎)
梦好莫催醒
 女帝表白失败,我被贬下凡间(兰有金乔归燕)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女帝表白失败,我被贬下凡间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兰有金乔归燕)
女帝表白失败,我被贬下凡间(兰有金乔归燕)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女帝表白失败,我被贬下凡间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兰有金乔归燕)
桃香鱼丸
 女帝表白失败,我被贬下凡间兰有金乔归燕最新完结小说推荐_全集免费小说女帝表白失败,我被贬下凡间兰有金乔归燕
女帝表白失败,我被贬下凡间兰有金乔归燕最新完结小说推荐_全集免费小说女帝表白失败,我被贬下凡间兰有金乔归燕
桃香鱼丸
 兰有金乔归燕(兰有金乔归燕)小说目录列表阅读-兰有金乔归燕最新阅读
兰有金乔归燕(兰有金乔归燕)小说目录列表阅读-兰有金乔归燕最新阅读
桃香鱼丸
 《退婚后,我和状元契约结婚了》叶珈段瑾免费完本小说在线阅读_《退婚后,我和状元契约结婚了》叶珈段瑾免费小说
《退婚后,我和状元契约结婚了》叶珈段瑾免费完本小说在线阅读_《退婚后,我和状元契约结婚了》叶珈段瑾免费小说
辣椒墩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