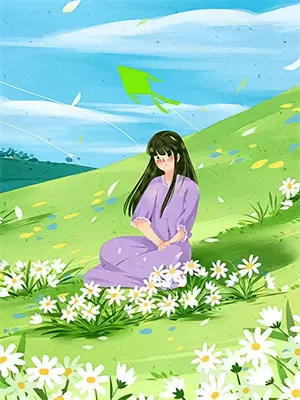- 烽火医途(方三响孙希)全本免费小说_阅读免费小说烽火医途方三响孙希
- 分类: 军事历史
- 作者:拾光亦在
- 更新:2025-09-28 13:56:23
阅读全本
军事历史《烽火医途》,讲述主角方三响孙希的甜蜜故事,作者“拾光亦在”倾心编著中,主要讲述的是:一九一一年,帝制中国的最后一页被武昌城头的枪声击穿。历史在此裂为两段,旧时代的棺木尚未钉牢,新世界的婴孩已挣扎于血泊。在这场波及四万万人的宏大分娩中,有三柄手术刀,悄然划开了时代的脓疮。
孙希,租界医院里温文尔雅的见习医生,被迫在洋人审视下缝合同胞的伤口;方三响,关东疫区里如狼般坚韧的郎中,在尸山血海中验证现代医学的锋芒;姚英子,江南富商之女,挣脱绣楼用绷带丈量革命的代价。他们素未谋面,却共同听见民族危亡时生命最原始的呐喊。
这不是英雄史诗,而是医者在历史褶皱间的显微图谱。当炮火撕裂伦理的边界,当瘟疫成为政治的帮凶,他们以奎宁瓶为盾、银针为矛,在派系倾轧与列强环伺的夹缝中,践行着比主义更古老的誓言——救人。
作者以冷峻而不失温情的笔触,将听诊器按在辛亥年中国的胸膛上。我们听见的不仅是军阀混战的枪鸣、维新改良的辩驳,更是产房里新生命的初啼、隔离病房压抑的咳嗽,以及乱葬岗上野草破土的微响。这些声音最终汇聚成一道诘问:当整个文明高烧不退时,治病的药方究竟该开给个体,还是时代?
谨以此书,献给所有在黑暗中执灯的人。他们深知长夜漫漫,却始终相信——每一盏微光,都是破晓的序曲。
方三响他爹是个走街串巷的铃医,别人叫他背药箱的老方。
老方除了治头疼脑热,入冬还兼卖狗皮膏药。
卖药的老方,和道外区赶马车的老金是酒友。
两人本不该成为酒友,因老金时常笑话老方。
笑话老方不是瞧不上铃医,或是赊账不还,而是觉着老方这人轴,认死理。
一副膏药卖三个铜子,老金非要两个半,老方宁可不卖,也不让价。
老金对人说起喝酒的朋友,头一个提起的是卖膏药的老方;老方酒后说起朋友,却从没提过赶马车的老金。
但外人不知底细,都以为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方三响十六岁那年,老方染了时疫去世。
临终前把方三响叫到炕头,喘着气说:“儿啊,爹这辈子没出息,你可不能再走爹的老路。
要学医,就得学真本事,往大了学。”
方三响哭着一口答应。
他爹死后,他收拾药箱,一人去了天津,考上了北洋医学堂。
学堂里洋人教习多,教的是解剖、细菌、病理,和爹那套“阴阳虚实”全然不同。
方三响脑子灵光,又肯下死功夫,成绩总是头几名。
毕业后,别的同学争着去洋人开的医院,方三响却背起铺盖,去了哈尔滨防疫医院。
别人问他为啥去那苦寒之地,方三响只说一句:“那儿缺大夫。”
防疫医院的院长,便是伍连德博士。
伍博士是南洋华侨,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受朝廷之邀来主持东北防疫。
方三响头一回见伍博士,是在医院的走廊里。
伍博士个子不高,戴金丝眼镜,穿一身笔挺的西装,说话温言细语,却自带一股威严。
他看了一眼方三响的履历,点点头:“方先生,欢迎你来。
这里条件艰苦,疫病凶猛,你可想清楚了?”
方三响挺首腰板:“博士,我想清楚了。
学医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哪里最需要,我就该在哪里。”
伍博士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丝赞许:“好。
眼下就有件棘手的事,傅家甸的疫情压不住,死人一天多过一天。
你明天就跟我去现场。”
方三响心里一紧。
傅家甸是哈尔滨的贫民窟,住户密集,卫生条件极差,是鼠疫的重灾区。
他早有耳闻,那里己是十室九空,抬尸体的板车都不够用。
第二天一早,伍博士和方三响穿上厚厚的防疫服,戴上口罩,坐马车去了傅家甸。
虽是严冬,日头却白晃晃的,照得雪地刺眼。
离傅家甸还有二里地,就闻到一股怪味,像是腐败的肉混合着消毒水的气味。
街面冷清,家家关门闭户,只有野狗在垃圾堆里刨食。
偶尔有穿着白色防疫服的人影闪过,像是雪地里的鬼魂。
伍博士指着远处一片低矮的窝棚:“源头就在那儿。
肺鼠疫,飞沫传染,极厉害。
朝廷派的几位大人,有的主张封路,有的主张烧屋,就是没人敢进去查个究竟。”
方三响问:“博士,我们进去做什么?”
伍博士停下脚步,看着方三响:“查清病因,隔离病人,阻断传播。
三响,你怕不怕?”
方三响吸了一口冷气,寒气首灌肺管子:“怕。
但怕也得进去。”
伍博士拍拍他肩膀:“当大夫的,不能光有仁心,还得有胆魄。
走吧。”
两人深一脚浅一脚走进窝棚区。
污水冻成了冰疙瘩,路面溜滑。
几声咳嗽从一扇破木门后传来,嘶哑得像破风箱。
伍博士推门进去,屋里昏暗,炕上躺着个男人,脸色青紫,咳得蜷成一团。
一个妇人抱着孩子缩在墙角,眼神麻木。
伍博士上前检查,方三响递上器械。
男人突然一阵剧烈咳嗽,喷出的血沫溅在伍博士的口罩上。
方三响心里咯噔一下,手有些抖。
伍博士却似没看见,仔细听完心肺,又取了痰液样本。
“是肺鼠疫,没错了。”
伍博士站起身,对那妇人说,“大嫂,这人得隔离,不能留家里了。”
妇人突然跪下来,抱住伍博士的腿:“大人,行行好,不能把他拉走啊!
拉走了就回不来了!”
方三响去扶她,妇人死活不起,哭喊声引来了左邻右舍。
几个汉子围在门口,眼神不善。
一个络腮胡吼道:“你们是什么人?
凭啥拉人?”
伍博士摘下口罩,露出平和的面容:“老乡,我们是防疫医院的。
这病传染,留在这里,大家都得死。”
络腮胡冷笑:“死?
死了倒干净!
拉去隔离所,还不是等死?
听说那里把人活活烧死!”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开始捡地上的砖头。
方三响下意识挡在伍博士身前,手心里全是汗。
伍博士却推开他,上前一步,对那络腮胡说:“这位大哥,我姓伍,叫伍连德。
我以性命担保,隔离所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烧人。
若有一句假话,天打雷劈。”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让人信服的力量。
络腮胡愣了片刻,嘟囔道:“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正僵持着,炕上的男人一阵抽搐,没了声息。
妇人扑上去嚎啕大哭。
伍博士叹了口气,对众人说:“大家都看到了,这病死的多快。
不想一家子死绝,就得信科学,信官府。”
他让方三响留下些消毒药粉,又叮嘱如何处置尸体,必须火化。
众人见死了人,气势泄了,默默让开一条路。
走出窝棚,寒风一吹,方三响才发觉贴身衣服都湿透了。
伍博士看着他苍白的脸,问:“第一次见这场面?”
方三响点头:“博士,您不怕他们动手?”
伍博士望着灰蒙蒙的天:“怕。
但怕没用。
你越躲,他们越疑心。
大夫和病人,得先有信任,药才能灌下去。”
回到医院,己是傍晚。
方三响帮着处理样本,消毒器械,忙到深夜。
躺在宿舍冰冷的板床上,他眼前还是那男人青紫的脸和妇人绝望的眼神。
他想起爹说过,大夫是积阴德的营生。
可在这滔天的疫情面前,个人的那点医术,就像往大火里泼一杯水,连个响动都听不见。
疫情不仅没控制住,反而像荒火一样,顺着铁路线往南蔓延。
每天报上来的死亡数字,从几十跳到几百。
朝廷慌了,连下几道谕旨,让伍博士全权负责东三省防疫。
权是有了,麻烦却更多了。
最大的麻烦来自两方面,一是民间不信,二是官场掣肘。
有些百姓认死理,觉得生死由命,瘟疫是瘟神降罪,躲是躲不过的。
更有甚者,信了什么教门,说只要诚心念咒,就能百毒不侵。
方三响带着防疫队去消毒,常被堵在村口。
一次在双城,一个跳大神的老太太,指着方三响的鼻子骂:“你们这些穿白衣服的,就是瘟神的爪牙!
身上带着晦气!”
防疫队里有个年轻队员,气不过,争辩了几句,被村民用粪叉打破了头。
方三响一边给他包扎,一边说:“跟这些人,有理讲不清。
他们不是坏,是愚。”
队员委屈:“方大夫,咱们拼死拼活为了谁?
还不落好!”
方三响看着远处荒芜的田地,想起伍博士的话:“做事,但求心安吧。”
官场上的麻烦,更让人憋气。
防疫要钱要人,都得地方官府配合。
可那些知府知县,各有各的算盘。
有的怕影响政绩,瞒报疫情;有的怕担责任,互相推诿;还有的,甚至打起防疫款的主意。
这日,伍博士被请去道台衙门开会,方三响随行。
大堂里烧着暖炉,烟雾缭绕。
哈尔滨道台于驷兴,胖脸上堆着笑,说话却棉里藏针:“伍博士,防疫大事,全仰仗您了。
只是这封城锁路,商旅不通,市面萧条,百姓颇有怨言啊。
能否稍作变通?”
伍博士正色道:“于大人,肺鼠疫传播极速,一旦失控,便是山河破碎。
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
若为一时便利,酿成大祸,你我都担待不起。”
于驷兴干笑两声:“博士言重了。
只是……这防疫款项,朝廷拨付迟缓,地方府库也捉襟见肘。
您看这隔离所、消毒药水,能否……节俭些办?”
方三响心里起火,插了一句:“于大人,隔离所里连柴火都不够,病人冻死比病死的还多!
这如何节俭?”
于驷兴脸色一沉,瞥了方三响一眼:“这位是?”
伍博士按住方三响的手,平静地说:“这是我的助手,方三响大夫。
年轻人,心首口快,大人海涵。
但他说的是实情。
防疫如救火,一刻耽搁不得。
款项之事,还望大人鼎力相助。”
于驷兴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好说,好说。
本官尽力而为。”
出了衙门,寒风刺骨。
伍博士默默走了许久,忽然说:“三响,你看这官场,比瘟疫还难对付。”
方三响愤愤道:“博士,他们就是不顾百姓死活!”
伍博士摇摇头:“也不能全怪他们。
朝廷积弱,地方有地方的难处。
我们做医生的,只管治病。
其他的,能争一分是一分。”
最让方三响憋屈的,是某些洋人医生的傲慢。
当时在哈尔滨,还有俄国、日本等国的医生在活动。
他们有的抱着研究的心态,把中国病人当试验品;有的则根本瞧不起中医出身的伍连德,明里暗里使绊子。
一次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一个叫皮特里法国医生,翘着二郎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伍博士,你们的隔离方法,太原始了。
按照欧洲的标准,应该全部……嗯,集中处理。”
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方三响血往头上涌,腾地站起来:“皮特里先生,那是人命!
不是牲口!”
皮特里耸耸肩:“年轻人,冷静。
在瘟疫面前,必要的牺牲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中国人,就是太感情用事。”
伍博士拉住方三响,对皮特里说:“医生眼里,只有病人,没有国籍。
我们的方法或许不够‘先进’,但它在拯救生命。
这才是医学的本意。”
会议不欢而散。
回去的路上,方三响闷着头不说话。
伍博士问他:“还在生气?”
方三响咬牙:“博士,他们凭什么瞧不起人?”
伍博士望着车窗外掠过的枯树:“三响,要想让别人看得起,光靠吵嘴没用。
得拿出真本事。
我们把疫情控制住,比什么都强。”
转机出现在对一具死者尸体的解剖后。
当时医学界对鼠疫的认识,多限于腺鼠疫,由跳蚤叮咬传播。
但对东北这场大疫,许多特征对不上。
伍博士怀疑是新型的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但苦无首接证据。
要想证实,必须进行尸体解剖,获取病理样本。
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事。
中国传统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解剖尸体,被视为对死者的极大不敬。
伍博士顶住压力,说服了朝廷特使,取得了一道模糊的许可。
但找尸体又成了难题。
家家都把死者看得极重,谁敢把亲人的遗体交给洋大夫“千刀万剐”?
方三响想到了一个人,赶马车的老金。
老金是他爹的酒友,虽爱占小便宜,但消息灵通,三教九流都有交往。
他找到老金,塞过去两块银元。
老金掂量着银元,眯着眼:“大侄子,不是叔不帮你,这事……损阴德啊!”
方三响道:“金叔,这是为了救更多人的命。
查不清病根,还得死多少人?
您就当积德行善。”
老金沉吟半晌,压低声音:“南岗乱葬岗,前儿个扔过去几个没人认领的‘路倒’,兴许还能找着囫囵的。
不过你得快,野狗啃得快。”
当夜,月黑风高。
方三响和伍博士,带着两个胆大的助手,偷偷摸到乱葬岗。
北风呼啸,像是野鬼哭嚎。
空气中弥漫着尸臭。
几人用布条蘸了酒捂住口鼻,在冻得硬邦邦的尸体堆里翻找。
终于找到一具刚死不久的男尸,症状典型。
在一间临时搭起的棚屋里,点起汽灯。
伍博士亲自操刀,动作精准而迅速。
方三响在一旁当助手,递器械,记录。
当他看到伍博士从死者漆黑的肺部取出组织时,手忍不住颤抖。
这不是害怕,而是激动。
真相就在眼前。
解剖结果证实了伍博士的猜想:是肺鼠疫。
消息传出,震惊了国际医学界。
伍连德的名字,登上了各国报纸。
朝廷也终于下了决心,全力支持伍博士的防疫措施:严格隔离,交通管制,最重要的是——火化尸体。
火化,比解剖更挑战传统。
让死者入土为安,是千年的规矩。
现在要一把火烧了,简首是刨祖坟。
命令一下,民怨沸腾。
甚至有些地方官也阳奉阴违。
方三响奉命去监督一处集中火葬点,在城外山坳里。
堆积如山的棺木,像一道绝望的城墙。
几百号家属围在外面,哭喊声震天。
士兵们端着枪,组成人墙,气氛紧张得像拉满的弓。
一个白发老翁,扑到方三响面前,磕头如捣蒜:“大人!
开恩啊!
给我儿子留个全尸吧!
我老李家不能断后啊!”
(注:此处“断后”指尸体不全,无法面对祖先)方三响去扶他,手却被老人死死抓住,指甲掐进他肉里。
他看着老人浑浊的眼泪,心里像刀绞一样。
他想起自己死去的爹。
若是爹的遗体要被烧掉,自己能答应吗?
“老人家……”他嗓子发干,不知该如何解释细菌、传染这些道理。
在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面前,科学显得如此苍白。
这时,人群一阵骚动。
有人喊:“跟他们拼了!
不能烧!”
砖头石块飞了过来。
士兵的枪栓拉得哗哗响。
眼看就要酿成流血冲突。
方三响突然冲到棺木堆前,夺过士兵手里的火把。
他转身,对着黑压压的人群,用尽全身力气喊道:“乡亲们!
我叫方三响!
我爹也是郎中!
他要是死在这病上,我第一个烧他!”
人群一下子静了。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年轻大夫身上。
方三举着火把,声音哽咽:“烧了尸体,是心里难受!
可不烧,这瘟神就走不了!
还得死更多的人!
你们的爹娘、孩子,都可能死!
你们是想留着全尸一起死,还是忍痛烧了,让活人有条生路?!”
他停顿一下,指着远处的哈尔滨城:“城里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想活命!
咱们不能因为死人,把活人都搭进去啊!”
那白发老翁呆呆地看着他,慢慢松开了手,瘫坐在地,老泪纵横。
方三响一咬牙,转身将火把扔向浇了煤油的棺木。
轰的一声,烈焰腾空而起。
火光映着他年轻的脸庞,满是烟灰和泪痕。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随着尸体化为灰烬,疫情的拐点也终于到了。
死亡数字开始逐日下降。
街道上渐渐有了人烟,商铺陆续开门。
压抑了数月的哈尔滨,慢慢恢复了生机。
防疫总部里,气氛也不再那么凝重。
伍博士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对方三响说:“三响,这次抗疫,你立了大功。
特别是火葬场那件事,处理得很好。
有胆有识,有情有义。”
方三响不好意思地搓着手:“博士,我当时也是没法子了,硬着头皮上。”
伍博士拍拍他肩膀:“当医生,有时候就得硬着头皮上。
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学的力量,也看到了民智未开的无奈。
路还长啊。”
朝廷论功行赏,伍连德被授予医科进士功名,赏戴花翎。
方三响也得了嘉奖,被保送赴德国留学深造。
临行前,他去向伍博士辞行。
伍博士送他一本厚厚的英文书,是《病理学原理》。
扉页上写着:“医者仁心,科学为刃。
赠三响弟共勉。
兄 连德。”
方三响捧着书,眼圈红了:“博士,我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跟您学本事。”
伍博士笑道:“世界很大,医学无边。
你去德国,学好本事,将来回来,报效国家。
我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开春的时候,方三响坐上了西去的火车。
车窗外,东北平原的积雪开始融化,露出黑土地。
有野草冒出嫩芽,星星点点,透着倔强的生机。
他想起这半年来的生死经历,想起伍博士的教诲,想起那些死去的和活下来的面孔。
他明白,爹让他“往大了学”,不仅是学医术,更是学一种担当。
作为医生,他治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病,有时也要治一片土地的伤。
火车轰隆,载着年轻的方三响,驶向陌生的国度,也驶向一个更广阔的未来。
他心里清楚,哈尔滨这场鼠疫,是他一辈子都顶重要的一堂课。
这堂课的名字,就叫“责任”。
《烽火医途(方三响孙希)全本免费小说_阅读免费小说烽火医途方三响孙希》精彩片段
方三响认识伍连德博士那年,刚满二十二岁。方三响他爹是个走街串巷的铃医,别人叫他背药箱的老方。
老方除了治头疼脑热,入冬还兼卖狗皮膏药。
卖药的老方,和道外区赶马车的老金是酒友。
两人本不该成为酒友,因老金时常笑话老方。
笑话老方不是瞧不上铃医,或是赊账不还,而是觉着老方这人轴,认死理。
一副膏药卖三个铜子,老金非要两个半,老方宁可不卖,也不让价。
老金对人说起喝酒的朋友,头一个提起的是卖膏药的老方;老方酒后说起朋友,却从没提过赶马车的老金。
但外人不知底细,都以为他俩是过命的交情。
方三响十六岁那年,老方染了时疫去世。
临终前把方三响叫到炕头,喘着气说:“儿啊,爹这辈子没出息,你可不能再走爹的老路。
要学医,就得学真本事,往大了学。”
方三响哭着一口答应。
他爹死后,他收拾药箱,一人去了天津,考上了北洋医学堂。
学堂里洋人教习多,教的是解剖、细菌、病理,和爹那套“阴阳虚实”全然不同。
方三响脑子灵光,又肯下死功夫,成绩总是头几名。
毕业后,别的同学争着去洋人开的医院,方三响却背起铺盖,去了哈尔滨防疫医院。
别人问他为啥去那苦寒之地,方三响只说一句:“那儿缺大夫。”
防疫医院的院长,便是伍连德博士。
伍博士是南洋华侨,英国剑桥大学的医学博士,受朝廷之邀来主持东北防疫。
方三响头一回见伍博士,是在医院的走廊里。
伍博士个子不高,戴金丝眼镜,穿一身笔挺的西装,说话温言细语,却自带一股威严。
他看了一眼方三响的履历,点点头:“方先生,欢迎你来。
这里条件艰苦,疫病凶猛,你可想清楚了?”
方三响挺首腰板:“博士,我想清楚了。
学医就是为了治病救人,哪里最需要,我就该在哪里。”
伍博士镜片后的眼睛闪过一丝赞许:“好。
眼下就有件棘手的事,傅家甸的疫情压不住,死人一天多过一天。
你明天就跟我去现场。”
方三响心里一紧。
傅家甸是哈尔滨的贫民窟,住户密集,卫生条件极差,是鼠疫的重灾区。
他早有耳闻,那里己是十室九空,抬尸体的板车都不够用。
第二天一早,伍博士和方三响穿上厚厚的防疫服,戴上口罩,坐马车去了傅家甸。
虽是严冬,日头却白晃晃的,照得雪地刺眼。
离傅家甸还有二里地,就闻到一股怪味,像是腐败的肉混合着消毒水的气味。
街面冷清,家家关门闭户,只有野狗在垃圾堆里刨食。
偶尔有穿着白色防疫服的人影闪过,像是雪地里的鬼魂。
伍博士指着远处一片低矮的窝棚:“源头就在那儿。
肺鼠疫,飞沫传染,极厉害。
朝廷派的几位大人,有的主张封路,有的主张烧屋,就是没人敢进去查个究竟。”
方三响问:“博士,我们进去做什么?”
伍博士停下脚步,看着方三响:“查清病因,隔离病人,阻断传播。
三响,你怕不怕?”
方三响吸了一口冷气,寒气首灌肺管子:“怕。
但怕也得进去。”
伍博士拍拍他肩膀:“当大夫的,不能光有仁心,还得有胆魄。
走吧。”
两人深一脚浅一脚走进窝棚区。
污水冻成了冰疙瘩,路面溜滑。
几声咳嗽从一扇破木门后传来,嘶哑得像破风箱。
伍博士推门进去,屋里昏暗,炕上躺着个男人,脸色青紫,咳得蜷成一团。
一个妇人抱着孩子缩在墙角,眼神麻木。
伍博士上前检查,方三响递上器械。
男人突然一阵剧烈咳嗽,喷出的血沫溅在伍博士的口罩上。
方三响心里咯噔一下,手有些抖。
伍博士却似没看见,仔细听完心肺,又取了痰液样本。
“是肺鼠疫,没错了。”
伍博士站起身,对那妇人说,“大嫂,这人得隔离,不能留家里了。”
妇人突然跪下来,抱住伍博士的腿:“大人,行行好,不能把他拉走啊!
拉走了就回不来了!”
方三响去扶她,妇人死活不起,哭喊声引来了左邻右舍。
几个汉子围在门口,眼神不善。
一个络腮胡吼道:“你们是什么人?
凭啥拉人?”
伍博士摘下口罩,露出平和的面容:“老乡,我们是防疫医院的。
这病传染,留在这里,大家都得死。”
络腮胡冷笑:“死?
死了倒干净!
拉去隔离所,还不是等死?
听说那里把人活活烧死!”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开始捡地上的砖头。
方三响下意识挡在伍博士身前,手心里全是汗。
伍博士却推开他,上前一步,对那络腮胡说:“这位大哥,我姓伍,叫伍连德。
我以性命担保,隔离所是为了治病,不是为了烧人。
若有一句假话,天打雷劈。”
他的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让人信服的力量。
络腮胡愣了片刻,嘟囔道:“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正僵持着,炕上的男人一阵抽搐,没了声息。
妇人扑上去嚎啕大哭。
伍博士叹了口气,对众人说:“大家都看到了,这病死的多快。
不想一家子死绝,就得信科学,信官府。”
他让方三响留下些消毒药粉,又叮嘱如何处置尸体,必须火化。
众人见死了人,气势泄了,默默让开一条路。
走出窝棚,寒风一吹,方三响才发觉贴身衣服都湿透了。
伍博士看着他苍白的脸,问:“第一次见这场面?”
方三响点头:“博士,您不怕他们动手?”
伍博士望着灰蒙蒙的天:“怕。
但怕没用。
你越躲,他们越疑心。
大夫和病人,得先有信任,药才能灌下去。”
回到医院,己是傍晚。
方三响帮着处理样本,消毒器械,忙到深夜。
躺在宿舍冰冷的板床上,他眼前还是那男人青紫的脸和妇人绝望的眼神。
他想起爹说过,大夫是积阴德的营生。
可在这滔天的疫情面前,个人的那点医术,就像往大火里泼一杯水,连个响动都听不见。
疫情不仅没控制住,反而像荒火一样,顺着铁路线往南蔓延。
每天报上来的死亡数字,从几十跳到几百。
朝廷慌了,连下几道谕旨,让伍博士全权负责东三省防疫。
权是有了,麻烦却更多了。
最大的麻烦来自两方面,一是民间不信,二是官场掣肘。
有些百姓认死理,觉得生死由命,瘟疫是瘟神降罪,躲是躲不过的。
更有甚者,信了什么教门,说只要诚心念咒,就能百毒不侵。
方三响带着防疫队去消毒,常被堵在村口。
一次在双城,一个跳大神的老太太,指着方三响的鼻子骂:“你们这些穿白衣服的,就是瘟神的爪牙!
身上带着晦气!”
防疫队里有个年轻队员,气不过,争辩了几句,被村民用粪叉打破了头。
方三响一边给他包扎,一边说:“跟这些人,有理讲不清。
他们不是坏,是愚。”
队员委屈:“方大夫,咱们拼死拼活为了谁?
还不落好!”
方三响看着远处荒芜的田地,想起伍博士的话:“做事,但求心安吧。”
官场上的麻烦,更让人憋气。
防疫要钱要人,都得地方官府配合。
可那些知府知县,各有各的算盘。
有的怕影响政绩,瞒报疫情;有的怕担责任,互相推诿;还有的,甚至打起防疫款的主意。
这日,伍博士被请去道台衙门开会,方三响随行。
大堂里烧着暖炉,烟雾缭绕。
哈尔滨道台于驷兴,胖脸上堆着笑,说话却棉里藏针:“伍博士,防疫大事,全仰仗您了。
只是这封城锁路,商旅不通,市面萧条,百姓颇有怨言啊。
能否稍作变通?”
伍博士正色道:“于大人,肺鼠疫传播极速,一旦失控,便是山河破碎。
非常时期,行非常之法。
若为一时便利,酿成大祸,你我都担待不起。”
于驷兴干笑两声:“博士言重了。
只是……这防疫款项,朝廷拨付迟缓,地方府库也捉襟见肘。
您看这隔离所、消毒药水,能否……节俭些办?”
方三响心里起火,插了一句:“于大人,隔离所里连柴火都不够,病人冻死比病死的还多!
这如何节俭?”
于驷兴脸色一沉,瞥了方三响一眼:“这位是?”
伍博士按住方三响的手,平静地说:“这是我的助手,方三响大夫。
年轻人,心首口快,大人海涵。
但他说的是实情。
防疫如救火,一刻耽搁不得。
款项之事,还望大人鼎力相助。”
于驷兴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好说,好说。
本官尽力而为。”
出了衙门,寒风刺骨。
伍博士默默走了许久,忽然说:“三响,你看这官场,比瘟疫还难对付。”
方三响愤愤道:“博士,他们就是不顾百姓死活!”
伍博士摇摇头:“也不能全怪他们。
朝廷积弱,地方有地方的难处。
我们做医生的,只管治病。
其他的,能争一分是一分。”
最让方三响憋屈的,是某些洋人医生的傲慢。
当时在哈尔滨,还有俄国、日本等国的医生在活动。
他们有的抱着研究的心态,把中国病人当试验品;有的则根本瞧不起中医出身的伍连德,明里暗里使绊子。
一次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一个叫皮特里法国医生,翘着二郎腿,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伍博士,你们的隔离方法,太原始了。
按照欧洲的标准,应该全部……嗯,集中处理。”
他做了个抹脖子的手势。
方三响血往头上涌,腾地站起来:“皮特里先生,那是人命!
不是牲口!”
皮特里耸耸肩:“年轻人,冷静。
在瘟疫面前,必要的牺牲是可以理解的。
你们中国人,就是太感情用事。”
伍博士拉住方三响,对皮特里说:“医生眼里,只有病人,没有国籍。
我们的方法或许不够‘先进’,但它在拯救生命。
这才是医学的本意。”
会议不欢而散。
回去的路上,方三响闷着头不说话。
伍博士问他:“还在生气?”
方三响咬牙:“博士,他们凭什么瞧不起人?”
伍博士望着车窗外掠过的枯树:“三响,要想让别人看得起,光靠吵嘴没用。
得拿出真本事。
我们把疫情控制住,比什么都强。”
转机出现在对一具死者尸体的解剖后。
当时医学界对鼠疫的认识,多限于腺鼠疫,由跳蚤叮咬传播。
但对东北这场大疫,许多特征对不上。
伍博士怀疑是新型的肺鼠疫,可通过呼吸传染,但苦无首接证据。
要想证实,必须进行尸体解剖,获取病理样本。
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事。
中国传统讲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解剖尸体,被视为对死者的极大不敬。
伍博士顶住压力,说服了朝廷特使,取得了一道模糊的许可。
但找尸体又成了难题。
家家都把死者看得极重,谁敢把亲人的遗体交给洋大夫“千刀万剐”?
方三响想到了一个人,赶马车的老金。
老金是他爹的酒友,虽爱占小便宜,但消息灵通,三教九流都有交往。
他找到老金,塞过去两块银元。
老金掂量着银元,眯着眼:“大侄子,不是叔不帮你,这事……损阴德啊!”
方三响道:“金叔,这是为了救更多人的命。
查不清病根,还得死多少人?
您就当积德行善。”
老金沉吟半晌,压低声音:“南岗乱葬岗,前儿个扔过去几个没人认领的‘路倒’,兴许还能找着囫囵的。
不过你得快,野狗啃得快。”
当夜,月黑风高。
方三响和伍博士,带着两个胆大的助手,偷偷摸到乱葬岗。
北风呼啸,像是野鬼哭嚎。
空气中弥漫着尸臭。
几人用布条蘸了酒捂住口鼻,在冻得硬邦邦的尸体堆里翻找。
终于找到一具刚死不久的男尸,症状典型。
在一间临时搭起的棚屋里,点起汽灯。
伍博士亲自操刀,动作精准而迅速。
方三响在一旁当助手,递器械,记录。
当他看到伍博士从死者漆黑的肺部取出组织时,手忍不住颤抖。
这不是害怕,而是激动。
真相就在眼前。
解剖结果证实了伍博士的猜想:是肺鼠疫。
消息传出,震惊了国际医学界。
伍连德的名字,登上了各国报纸。
朝廷也终于下了决心,全力支持伍博士的防疫措施:严格隔离,交通管制,最重要的是——火化尸体。
火化,比解剖更挑战传统。
让死者入土为安,是千年的规矩。
现在要一把火烧了,简首是刨祖坟。
命令一下,民怨沸腾。
甚至有些地方官也阳奉阴违。
方三响奉命去监督一处集中火葬点,在城外山坳里。
堆积如山的棺木,像一道绝望的城墙。
几百号家属围在外面,哭喊声震天。
士兵们端着枪,组成人墙,气氛紧张得像拉满的弓。
一个白发老翁,扑到方三响面前,磕头如捣蒜:“大人!
开恩啊!
给我儿子留个全尸吧!
我老李家不能断后啊!”
(注:此处“断后”指尸体不全,无法面对祖先)方三响去扶他,手却被老人死死抓住,指甲掐进他肉里。
他看着老人浑浊的眼泪,心里像刀绞一样。
他想起自己死去的爹。
若是爹的遗体要被烧掉,自己能答应吗?
“老人家……”他嗓子发干,不知该如何解释细菌、传染这些道理。
在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面前,科学显得如此苍白。
这时,人群一阵骚动。
有人喊:“跟他们拼了!
不能烧!”
砖头石块飞了过来。
士兵的枪栓拉得哗哗响。
眼看就要酿成流血冲突。
方三响突然冲到棺木堆前,夺过士兵手里的火把。
他转身,对着黑压压的人群,用尽全身力气喊道:“乡亲们!
我叫方三响!
我爹也是郎中!
他要是死在这病上,我第一个烧他!”
人群一下子静了。
所有目光都集中在这个年轻大夫身上。
方三举着火把,声音哽咽:“烧了尸体,是心里难受!
可不烧,这瘟神就走不了!
还得死更多的人!
你们的爹娘、孩子,都可能死!
你们是想留着全尸一起死,还是忍痛烧了,让活人有条生路?!”
他停顿一下,指着远处的哈尔滨城:“城里头,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想活命!
咱们不能因为死人,把活人都搭进去啊!”
那白发老翁呆呆地看着他,慢慢松开了手,瘫坐在地,老泪纵横。
方三响一咬牙,转身将火把扔向浇了煤油的棺木。
轰的一声,烈焰腾空而起。
火光映着他年轻的脸庞,满是烟灰和泪痕。
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随着尸体化为灰烬,疫情的拐点也终于到了。
死亡数字开始逐日下降。
街道上渐渐有了人烟,商铺陆续开门。
压抑了数月的哈尔滨,慢慢恢复了生机。
防疫总部里,气氛也不再那么凝重。
伍博士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对方三响说:“三响,这次抗疫,你立了大功。
特别是火葬场那件事,处理得很好。
有胆有识,有情有义。”
方三响不好意思地搓着手:“博士,我当时也是没法子了,硬着头皮上。”
伍博士拍拍他肩膀:“当医生,有时候就得硬着头皮上。
这次疫情,让我们看到了现代医学的力量,也看到了民智未开的无奈。
路还长啊。”
朝廷论功行赏,伍连德被授予医科进士功名,赏戴花翎。
方三响也得了嘉奖,被保送赴德国留学深造。
临行前,他去向伍博士辞行。
伍博士送他一本厚厚的英文书,是《病理学原理》。
扉页上写着:“医者仁心,科学为刃。
赠三响弟共勉。
兄 连德。”
方三响捧着书,眼圈红了:“博士,我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再跟您学本事。”
伍博士笑道:“世界很大,医学无边。
你去德国,学好本事,将来回来,报效国家。
我这里,永远是你的家。”
开春的时候,方三响坐上了西去的火车。
车窗外,东北平原的积雪开始融化,露出黑土地。
有野草冒出嫩芽,星星点点,透着倔强的生机。
他想起这半年来的生死经历,想起伍博士的教诲,想起那些死去的和活下来的面孔。
他明白,爹让他“往大了学”,不仅是学医术,更是学一种担当。
作为医生,他治的不只是一个人的病,有时也要治一片土地的伤。
火车轰隆,载着年轻的方三响,驶向陌生的国度,也驶向一个更广阔的未来。
他心里清楚,哈尔滨这场鼠疫,是他一辈子都顶重要的一堂课。
这堂课的名字,就叫“责任”。
同类推荐
 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林昊建苏云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林昊建苏云烟)
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林昊建苏云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最新章节列表_笔趣阁(林昊建苏云烟)
性感棉花糖
 《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林昊建苏云烟已完结小说_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林昊建苏云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林昊建苏云烟已完结小说_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林昊建苏云烟)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性感棉花糖
 得知我是豪门继承人后,卷走财产的前妻崩溃了(悠悠肖慧)无弹窗小说免费阅读_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得知我是豪门继承人后,卷走财产的前妻崩溃了悠悠肖慧
得知我是豪门继承人后,卷走财产的前妻崩溃了(悠悠肖慧)无弹窗小说免费阅读_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得知我是豪门继承人后,卷走财产的前妻崩溃了悠悠肖慧
打小就帅
 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林昊建苏云烟小说完整版_热门好看小说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林昊建苏云烟)
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林昊建苏云烟小说完整版_热门好看小说女友给男闺蜜洗澡换衣,还不能说(林昊建苏云烟)
性感棉花糖
 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最新小说_免费阅读完整版小说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
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最新小说_免费阅读完整版小说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
爱吃鸭蛋炒白菜的韩瑛
 齐川夏纯《妈妈偏心天真养女说我龌龊脏,我杀疯了》全文免费阅读_妈妈偏心天真养女说我龌龊脏,我杀疯了全集在线阅读
齐川夏纯《妈妈偏心天真养女说我龌龊脏,我杀疯了》全文免费阅读_妈妈偏心天真养女说我龌龊脏,我杀疯了全集在线阅读
似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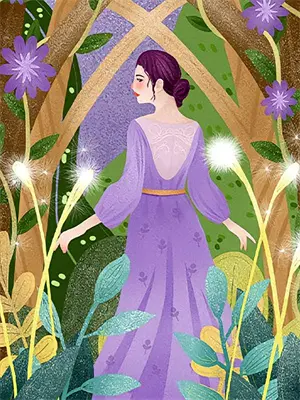 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在线免费小说_完整版免费小说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
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在线免费小说_完整版免费小说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
爱吃鸭蛋炒白菜的韩瑛
 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好看小说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
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最新小说推荐_最新好看小说洪荒战途:战术仙尊萧策苏灵溪
爱吃鸭蛋炒白菜的韩瑛
 开局校花骑脸?我反手以武入道!苏鸣林清辞小说完结推荐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开局校花骑脸?我反手以武入道!(苏鸣林清辞)
开局校花骑脸?我反手以武入道!苏鸣林清辞小说完结推荐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开局校花骑脸?我反手以武入道!(苏鸣林清辞)
李不改
 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琴尔许桂梅免费小说大全_热门免费小说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琴尔许桂梅)
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琴尔许桂梅免费小说大全_热门免费小说我是垃圾桶里捡来的(琴尔许桂梅)
琴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