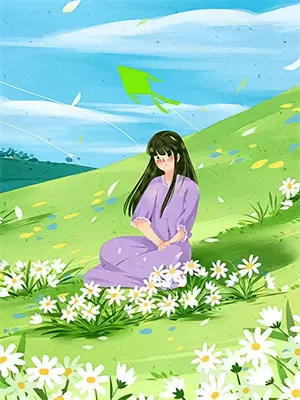- 离婚笑看扶弟魔求饶小明小丽全本免费完结小说_免费小说完结离婚笑看扶弟魔求饶小明小丽
- 分类: 都市小说
- 作者:云织熙梦
- 更新:2025-07-29 11:57:17
《离婚笑看扶弟魔求饶小明小丽全本免费完结小说_免费小说完结离婚笑看扶弟魔求饶小明小丽》精彩片段
我叫李明,今年30岁,是个普通的程序员,在北京一家小科技公司上班,月薪税后8000块。说实话,在帝都,刨去房租水电,也就勉强够我一个人糊口。但要养家糊口,就得靠拼命加班、接项目赚外快来撑着。回想三年前,我和小丽结婚的时候,一切都像是场甜蜜的梦。那时候,我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另一半,一个同样努力、温柔体贴的妻子,我们一起在那间小小的出租屋里,满怀希望地规划着未来。
一切要从我们的相识说起。那是五年前,我大学毕业后刚进公司,干着最基础的开发工作,每天敲代码到深夜。小丽在对面写字楼的一家广告公司做行政文员,月薪大概7000块,比我小两岁。我们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那天聚会的灯光有些晃眼,她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连衣裙,素净得像雨后初晴的天空,笑着递给我一杯咖啡:“李明,你看起来好累啊,多喝点提神。”她的笑容带着一种安静的暖意,像春风吹散了连日加班的疲惫。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女孩不一样。她不爱扎堆凑热闹,不追名牌包包,最大的爱好是周末去朝阳公园的长椅上看一下午书,或者就只是安静地散散步。或许就是这份沉静体贴,抚慰了我日日紧绷的神经,我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谈了两年,便决定结婚。
婚礼很简单,就在老家办了个小酒席。我父母是传统的工厂工人,退休后靠养老金过日子。他们攒了大半辈子钱,东拼西凑拿出了10万块,其中一部分用于给女方家的彩礼象征性地给了2万,大部分又让我们带了回来,剩下的几万块,是他们给我攒的首付启动资金。小丽的父母是农村出来的,在城里打零工,家境普通。她说:“明哥,我不图钱,就图你人好。”当时我感动坏了,觉得娶到她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婚后,我们在北京远郊租了个一室一厅的小公寓,每月房租2000块。我每天早出晚归,加班写代码,她下班早,总能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等我。晚上,我们一起挤在沙发上追剧,更多的是在网上反复浏览远郊的楼盘信息,计算着需要多少首付,每月要还多少房贷。那时候,我总对她说:“小丽,北京房价高,但咱们努力两年,就能凑够首付,买个小窝,安个家,生个孩子。”她总是点头,眼里闪着光:“嗯,明哥,我们一起努力,日子会好的。”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着,看起来平淡却充满希望。可渐渐地,一些不对劲的苗头开始冒出来。起初是家里开支总是不够用。我工资8000,她7000,加起来税后15000。房租2000,水电煤网算500,两人吃饭自己做饭为主,偶尔外卖按北京这物价,精打细算也得4000-4500,交通地铁通勤+偶尔打车1000,手机费网费200,日用品杂费洗漱、清洁等500。这已经是抠着算了:2000 + 500 + 4500 + 1000 + 200 + 500 = 8700元。15000 - 8700 = 6300元。按理说,每个月怎么也该能存下几千块。可现实是,从婚后第一个月开始,月底小丽就告诉我超支了300多。我记得有一次周末去超市大采购,我负责推车,她拿着清单精挑细选,预算500块。结果结账时,屏幕上跳出600多。小丽看着账单,眉头微蹙:“这排骨和水果怎么又贵了?”她语气有点懊恼,“都怪我,没看仔细价签。”我虽然觉得有点多,但看她自责的样子,就摆摆手:“没事,物价涨嘛,从我那份零花钱里扣。”毕竟,那时候疫情刚过去没多久,手机推送的新闻全是“XX蔬菜价格同比上涨XX%”,我也只能无奈地叹口气,把这归咎于疫情后遗症和帝都高昂的生活成本,以为这就是常态。
为了尽快填上那个“首付”的窟窿,我开始拼命加班。公司有项目,我就主动接,项目紧的时候,熬通宵也是常事。凌晨两三点拖着灌了铅的双腿回家,小丽总会给我热好饭菜,轻轻按摩我僵硬的肩膀,柔声说:“明哥,你辛苦了。”那一刻,身体的透支似乎都值得了。周末我们偶尔出去打打牙祭,吃顿火锅。点菜时,她总是一遍遍比较价格,最后只点一个锅底、两盘特价肉和一份青菜,念叨着:“省着点,花在买房上。”看着她为省几块钱精打细算的样子,听着她“省着点买房”的念叨,我胸口那点积压的疲惫和身体发出的警报开始频繁心悸,眼前有时会短暂发黑,对着电脑屏幕久了,眼睛干涩刺痛得厉害,滴眼药水也不大管用,都被一股更强烈的责任感和愧疚感压了下去。她是这么懂事,我有什么理由不拼命?医生说是过度劳累,警告我注意身体。可我咬着牙,目标像灯塔一样清晰:攒够首付,买个小房子,安稳下来。这念头支撑着我。
回想我的童年,或许这“拼命”和“忍耐”的根,就深扎在那里。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工厂工人,爸爸在流水线上干了一辈子,妈妈操持家务带大我。他们教给我的第一课就是“忍让是美德”。小时候邻居孩子抢我的玩具,爸爸说:“让让他吧,和气生财。”上学被同学欺负,妈妈劝:“忍忍就过去了,别惹事。”这种教育像刻刀,把我塑造成了一个习惯性把委屈和疑问咽回肚子里的老好人,视冲突为洪水猛兽。大学谈过一次恋爱,那女孩嫌我工资低没前途,转身就走。我连挽留的话都没说出口,只是默默接受,那份被现实否定的刺痛感一直埋在心底。遇到小丽时,她那句“不图钱就图你人好”,让我觉得她就是我的救赎。所以,婚前她偶尔回趟娘家,总会带些东西,有时是水果点心,有时是给家里买的日用品,金额不大,我也觉得是人之常情,从未细问。记得有一次,她妈打电话来,说弟弟小明想换个手机,她当着我的面就转了500过去。我说:“孝顺父母,帮衬家里,应该的。”当时我忽略了,这其实是个伏笔。婚后,她回娘家的频率越来越高,带回去的东西渐渐变成了现金,从最初的三五百,到后来动辄一两千。理由是“家里修房子”、“弟弟学费”、“妈妈看病抓药”。每次话到嘴边,看着她略带疲惫却强撑的笑脸,再想想她平时为小家省吃俭用的样子,还有那句“不图钱就图你人好”,我那点疑虑就像被针戳破的气球,泄了气。“算了,”我对自己说,“孝顺父母没错,她也不容易,别为这点钱伤了和气。”父母的“忍让”教诲仿佛刻在骨子里,成了我逃避冲突的本能。
就这样,在外人甚至我自己努力维持的想象里,这日子依然是甜蜜的。每天早上六点,我挣扎着起床,赶早高峰的地铁。小丽七点出门,我们在狭小的玄关匆匆吻别。她下班早,总能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晚上我加班回来,无论多晚,她会泡杯温热的茶,陪我聊聊。话题离不开工作压力和那个共同的梦:反复计算着存款距离远郊那个看中的小两居首付还差多少,盘算着哪里的房子性价比更高。我说:“小丽,北京房价是座山,但咱们努力两年,肯定能翻过去。”她点头:“嗯,我支持你。”那些日子,生活像绷紧的弦,但有盼头。疫情期间,公司一度减薪,我月薪降到6000。她也愁眉苦脸地说公司效益不好,奖金停了,日子更紧巴。我们互相打气,硬是挺了过来。有一次,她红着眼圈说信用卡还不上,一时没忍住打折多买了两件冬装。我看着她少有的“任性”,反而有点心疼,二话不说就用自己攒的钱帮她填上了窟窿,还安慰她:“没事,偶尔买点喜欢的应该的。”帮她转账时,心里那根刺又冒了出来。以她平时的节俭,怎么会一下子花超这么多?但看着她如释重负、对我充满感激的眼神,再想到疫情下大家都不容易,我硬是把疑问压了下去。‘夫妻嘛,’我告诉自己,‘信任最重要。’
可经济上的警报却越来越刺耳。在预期月余6300的基础上,第一个月超支200;第二个月,缺口变成了400;第三个月,直接超了800!我开始学着记账,一项项核对。发现超市购物小票上的金额确实比以前高,尤其是肉类、水果和一些日用品。标注着“特价”的东西,单价似乎也比记忆中的贵了。我对小丽说:“咱们得再省省了。”她答应了,但月底的数字依旧难看。我翻着手机里各种“物价上涨”的新闻,试图说服自己:这是疫情后遗症,北京的通胀压力大,大家都一样勒紧裤腰带。朋友小刚,我的大学同学,现在同公司做项目组长,看我脸色蜡黄,忧心忡忡:“老李,你这脸色可不对啊,嫂子那工资…加上你的,按理不该这么紧吧?你是不是该盘盘账?”我勉强笑笑:“没事,物价高嘛,忍忍就过去了。”心里却有个声音在反驳:小丽那么省,还能是她的问题?肯定是这该死的物价和我赚得还不够多!
有一次,我们计划了好久,打算去京郊爬爬山,透透气,连零食和水都提前买好了放在玄关。临出门,小丽手机响了,是她妈。挂了电话,她一脸焦急:“明哥,对不住,我得回趟娘家。小明电话里哭得厉害,找工作又碰壁了,我得回去看看,开导开导他。”小明是她弟弟,25岁,比她小三岁,据说在老家一直高不成低不就,疫情期间更是闲到现在。我没多想:“去吧,路上小心,早点回来。”她匆匆忙忙地,除了吃的,还从放现金的抽屉里拿了大概两千块钱塞进包里。那天我一个人在家,看着玄关处准备好的郊游背包,再看看瞬间冷清下来的屋子,一种难以言喻的疲惫和孤单涌上来,比加班到凌晨还要累。弟弟遇到困难,她回去看看是应该的,我怎么能这么小心眼?我摇摇头,试图甩掉那点不该有的情绪。
日子在加班的陀螺中飞转。公司接了个大项目,我主动报名,通宵成了家常便饭。回家后常常倒头就睡。小丽体贴地不吵我,默默帮我洗掉沾满汗味的工服,做好早餐温在锅里。可账单的窟窿像个无底洞。有个月底,我强打精神算了算账。这个月没有额外的人情支出,按照日常开销和我的加班费,共同账户里本该剩下至少3000块作为储蓄。可手机银行APP上,刺眼的余额显示:1072.58元。巨大的落差让我心慌。我问小丽:“钱怎么花这么快?”她正在叠衣服的手顿了一下,随即叹了口气:“唉,我也觉得奇怪。这个月燃气费比上个月多了一百多,菜价涨得离谱,楼下超市连卫生纸都贵了五块。我看了都心惊。”她走过来,带着点歉意看着我,“下个月我仔细点,多跑几个菜市场比价。” 我看着她疲惫的神情,那句追问卡在喉咙里,最终只化作一句:“嗯,辛苦你了。” 心里却有个声音在说:或许真是这样吧,大家都难。然而,又一次通宵后,我头痛欲裂地回到家,看到手机银行APP上又一次触目惊心的余额提醒——比预期又少了一大截。冷水澡也冲不散那股深入骨髓的烦躁。靠在冰冷的瓷砖墙上,不知怎的,婚前那次她给她弟转手机钱时,那熟练又理所当然的样子,突然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当时觉得是小事,是孝顺。可现在,无数个“小事”像滚雪球一样,变成了压得我喘不过气的巨大窟窿。父母的“忍让”像一道紧箍咒,箍得我连开口问个明白的勇气都没有。可这沉默的包容,到底是在维系家庭,还是在纵容一个看不见的黑洞,把我们共同的未来一点点吞噬?
转眼间,结婚一年了。我们依然蜗居在出租屋里。靠着我玩命加班、近乎苛刻地压缩个人开销午饭啃馒头是常事,硬是从牙缝里抠出了5万块,加上父母给的那几万启动资金,离那个远郊小两居的首付似乎近了一步。小丽也总说“我也在努力攒着呢”。可有次路过银行,她顺便查了下工资卡余额,我无意中瞥见屏幕——只有三位数。我问:“你工资呢?”她眼神闪烁了一下,含糊地说:“哦,日常开销呗,还有…家里一些零碎用度。” “家里?”哪个家?但我看着她迅速别开的脸和紧抿的嘴唇,那句追问终究被咽了回去。算了,追问又能怎样?吵一架吗?现在项目到了关键期,公司裁员风声鹤唳,我经不起分心。疫情的阴影像低垂的乌云,从未真正散去。
每天挤在沙丁鱼罐头般的地铁里,我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冰冷高楼,巨大的玻璃幕墙反射着灰蒙蒙的天。北京这么大,繁华触手可及,却又遥不可及。小丽疲惫却温柔的笑脸,是我在这座钢筋森林里熬下去的唯一甜味剂。我不能、也不敢去深想那“像流水一样溜走”的钱究竟去了哪里。深想,可能就是万丈深渊。除了“忍”,除了更拼命地加班,用透支身体去填补那个似乎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我还能做什么?“买房安家”这四个字,像遥远的海市蜃楼,是我在麻木忍耐中唯一能抓住的稻草,支撑着我机械地向前挪动脚步。
日子在表面的平静下,暗流汹涌。风暴的前兆,在一个加班的深夜显露。我拖着几乎散架的身体推开家门,客厅只亮着一盏昏暗的小夜灯。小丽蜷在沙发上睡着了,呼吸均匀。餐桌上,一张超市购物小票随意地摊开着。鬼使神差地,我拿了起来。目光扫过总额栏——785.60元。我的血瞬间凉了半截。这个金额,足够我们平时一周的伙食费!再看明细:进口车厘子、精品牛排、高档巧克力……全是我们平时绝对不会买、也买不起的东西!东西呢?冰箱里依旧是那几样普通的蔬菜。一股寒意从脚底直冲头顶。真的只是物价问题吗?还是……这张小票,像一根冰冷的导火索,瞬间引爆了积压已久的怀疑。
我没吵醒她,轻手轻脚走进卧室。那一夜,我彻底失眠了。黑暗中,天花板上的纹路仿佛变成了扭曲的数字和巨大的问号。小丽均匀的呼吸声就在隔壁,曾经是安眠曲,此刻却像一种无声的控诉。那张刺眼的小票、弟弟永远找不顺的工作、她卡上消失的工资、我越来越沉重的心悸和模糊的视线、还有那个在账单黑洞中越来越飘渺的“家”……所有零碎的疑点,在这个死寂的夜里,像冰冷的潮水,一浪接一浪地猛烈拍打着我一直以来筑起的、摇摇欲坠的“信任”堤坝。那根扎在心底的刺,终于变成了搅动五脏六腑的、令人窒息的钝痛。
“‘忍忍吧,’”我对着无边的黑暗,像念着父母刻在我骨子里的咒语,声音干涩而微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会好的…”
可心底,一个冰冷的声音带着绝望的颤音,尖锐地刺破了这苍白的自我安慰:
真的吗?
同类推荐
 沈甜林宴《情难两全》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沈甜林宴)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沈甜林宴《情难两全》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沈甜林宴)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苏三四
 重生后我主动回村,他们却悔疯了春山杜元全本免费小说_热门网络小说推荐重生后我主动回村,他们却悔疯了春山杜元
重生后我主动回村,他们却悔疯了春山杜元全本免费小说_热门网络小说推荐重生后我主动回村,他们却悔疯了春山杜元
春山拥飞燕
 天降一千万后,全家要献祭我福报村陈朗完整版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天降一千万后,全家要献祭我(福报村陈朗)
天降一千万后,全家要献祭我福报村陈朗完整版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天降一千万后,全家要献祭我(福报村陈朗)
长晔
 迹月成名江屿《帮邻居遛狗后,我倒欠他几百万》完结版免费阅读_迹月成名江屿热门小说
迹月成名江屿《帮邻居遛狗后,我倒欠他几百万》完结版免费阅读_迹月成名江屿热门小说
迹月
 开局直播间砸二十万,我让闺蜜倾家荡产(陈锋孙晓)最热门小说_全本完结小说开局直播间砸二十万,我让闺蜜倾家荡产(陈锋孙晓)
开局直播间砸二十万,我让闺蜜倾家荡产(陈锋孙晓)最热门小说_全本完结小说开局直播间砸二十万,我让闺蜜倾家荡产(陈锋孙晓)
佚名
 弟弟替我恋了男友傅祈傅祈免费小说笔趣阁_完结小说免费阅读弟弟替我恋了男友傅祈傅祈
弟弟替我恋了男友傅祈傅祈免费小说笔趣阁_完结小说免费阅读弟弟替我恋了男友傅祈傅祈
玖日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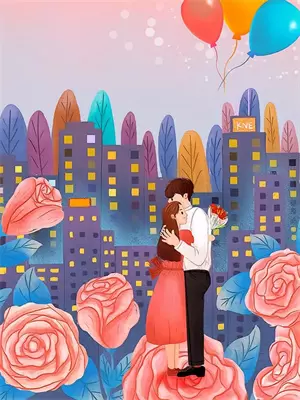 花了100万娶的媳妇,不到一个月就跑了张伟王莉免费小说完结_最新完本小说推荐花了100万娶的媳妇,不到一个月就跑了(张伟王莉)
花了100万娶的媳妇,不到一个月就跑了张伟王莉免费小说完结_最新完本小说推荐花了100万娶的媳妇,不到一个月就跑了(张伟王莉)
玖日故事
 重生错了人,请全班狂欢的假千金慌了林浩柳如烟免费热门小说_最热门小说重生错了人,请全班狂欢的假千金慌了林浩柳如烟
重生错了人,请全班狂欢的假千金慌了林浩柳如烟免费热门小说_最热门小说重生错了人,请全班狂欢的假千金慌了林浩柳如烟
玖日故事
 无根老公选过喜新娘解毒,我转身找竹马生娃林卿卿陆九渊完整版在线阅读_林卿卿陆九渊完整版阅读
无根老公选过喜新娘解毒,我转身找竹马生娃林卿卿陆九渊完整版在线阅读_林卿卿陆九渊完整版阅读
玖日故事
 王莉江阳《亡夫五百万遗产,儿媳假死骗我入局》全文免费阅读_亡夫五百万遗产,儿媳假死骗我入局全集在线阅读
王莉江阳《亡夫五百万遗产,儿媳假死骗我入局》全文免费阅读_亡夫五百万遗产,儿媳假死骗我入局全集在线阅读
玖日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