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隐居十年冰冷阿萦免费完结版小说_小说完结隐居十年冰冷阿萦
- 分类: 言情小说
- 作者:东方逆鳞
- 更新:2025-07-26 03:54:18
《隐居十年冰冷阿萦免费完结版小说_小说完结隐居十年冰冷阿萦》精彩片段
豆大的雨点砸在屋顶的茅草上,噼啪作响,像是无数双手在急促地拍打。山谷深处,这座被唤作“忘忧”的茅屋,在狂风骤雨中飘摇。油灯如豆,我用手护住昏黄的光晕,灯影在墙壁上摇晃,映着手中那卷早已翻烂的《南华经》。十年了,字海中的逍遥游,依旧没能洗去指腹握剑留下的薄茧。
“咚!咚!咚!”
敲门声突兀地炸响,盖过了风雨的喧嚣。带着一种濒死的蛮力,撞得门板簌簌发抖。
我搁下书卷,指尖无意识地擦过腰间那截空悬的剑鞘——鞘已蒙尘,鞘内却空空如也。门栓拉开一道缝隙,一股裹挟着浓烈血腥气的湿冷腥风猛地灌了进来。
门口瘫倒着一团模糊的人形。
她单薄的衣裙被雨水和血污浸透,紧贴在瘦削的身体上,勾勒出惊心动魄的伶仃。雨水混着暗红的血水,顺着她贴在脸颊上的乌发蜿蜒而下。她仰着脸,雨水冲刷着那张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只有那双眼睛,在闪电骤然劈开的惨白光芒中,亮得惊人,像燃烧着最后一点炭火的余烬,死死钉在我脸上。
“救……救……”破碎的音节从她青紫的唇间艰难挤出,每一个字都耗尽了她仅存的气力。话未说完,她身体猛地一软,向前栽倒。我下意识地伸手一抄,将她冰冷湿透的身子揽住。轻叹一声。
入手一片黏腻滚烫,是血。她倒在我的臂弯里,气息微弱得如同游丝。我将她抱进屋内,侧放在屋内唯一的竹榻上,她后背的刀伤被雨水冲得发白。油灯凑近,才看清她左肩衣衫破碎处,一个烙铁留下的印记清晰可辨——三朵妖异的缠枝莲,这是……
玉香楼的烙印。我的心沉了沉。指尖搭上她冰冷的手腕,微弱得几乎断绝的脉息下,一股极其阴寒、刁钻的气息却在隐隐窜动。我轻轻掰开她紧攥的右手。
掌心血肉模糊,赫然嵌着三根细如牛毛的乌黑短针!针尾微微颤动,周围的皮肉已呈现出一种令人心悸的紫黑色,正丝丝缕缕地向四周蔓延,散发着淡淡的、带着铁锈和腐败甜腥的诡异气味。
蚀骨针!十年前,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鬼门十三煞”的独门暗器!中者如万蚁噬骨,十二个时辰内筋骨寸断而亡,歹毒无比。此毒虽非无解,但所需药材极其罕见,炼制解药的手法更是繁复艰难,非一时之功。
她怎么会惹上这群早已销声匿迹的煞星?
“他们……追来了……”榻上的女子在昏迷的边缘挣扎,身体剧烈地抽搐了一下,长睫沉重地掀开一丝缝隙,那点微弱的光亮死死锁住我,冰冷的手指如同铁钳般猛地攥紧了我的衣角,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求你……别丢下我……”
话音未落,那点光亮彻底熄灭,她头一歪,彻底陷入死寂般的昏迷,只有那只攥着我衣角的手,依旧固执地紧握着,仿佛那是她沉入无边黑暗前抓住的唯一浮木。我给她处理了后背的伤口,终于止住了血。
窗外,风雨声似乎骤然猛烈了几分。我掰开她紧攥住衣角的手,起身走向屋角那个蒙尘的药柜。蚀骨针毒,霸道阴狠,拖延不得。几味主药,赤须藤、寒潭冰魄草、百年老参……还好,这十年避世,旁的或许荒废,当年师门传承的医术和采备的奇药,倒还存着一些。
药罐在红泥小炉上咕嘟作响,苦涩的药气弥漫开来,暂时压住了屋内的血腥。我守着炉火,凝视着跳动的火苗。玉香楼的烙印,鬼门十三煞的蚀骨针……这女子身上纠缠的谜题,像一张无形的大网,正悄无声息地罩向我。
“忘忧?”我咀嚼着这两个字,唇边溢出一丝冰冷的自嘲。窗外,风雨如晦,沉沉地压着山谷。
药气氤氲,苦涩中带着一丝微凉的奇异气息。我小心翼翼地撇去药罐边缘的浮沫,炉火映着竹榻上那张毫无生气的脸。她的右手无力地垂在榻边,手腕处露出一截褪色发白的红绳。那红绳编织得有些歪扭,显然不是出自匠人之手,绳结的样式……
我的目光骤然凝固。
十年前,那个同样飘着冷雨的黄昏,我浑身浴血,踉跄着扑进家门,入目便是冲天烈焰。小妹倒在血泊中,小小的身体冰冷僵硬,唯有她纤细的手腕上,系着几乎一模一样的、由我亲手为她编的红绳……那根红绳,连同她最后惊恐绝望的眼神,是我十年来无法挣脱的梦魇。
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眼前瞬间弥漫开一片血红。炉火哔剥一声轻响,才将我从那窒息般的幻象中惊醒。指尖不受控制地微微颤抖,几乎握不稳手中的药勺。
就在这时——
“咻!咻咻咻!”
数点寒星穿透窗纸,带着凄厉的哨音,狠狠钉入屋内的泥墙和木柱之上!力道之大,入木后尾羽犹自嗡嗡震颤。是弩箭!冰冷的杀意如同倒灌的寒风,瞬间弥漫了整个狭小的空间。
紧接着,沉重的脚步声踏碎了泥泞,由远及近,密密麻麻地围拢过来,将茅屋围得水泄不通。脚步声沉重而整齐,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压迫感。
“砰!”
一声巨响,简陋的柴扉被一股巨力从外面猛地踹开,木屑四散飞溅。门外,影影绰绰立着十数条黑色的身影,如同从地狱爬出的恶鬼,无声地矗立在黑暗里。为首一人身材高大,缓步踏入屋内,雨水顺着玄黑的斗笠边缘滴落,砸在铺地的木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他摘下斗笠,露出一张布满刀疤的狞恶面孔,鹰隼般的目光带着毫不掩饰的轻蔑和残忍,扫过简陋的屋内,最终定格在竹榻上昏迷的女子身上,嘴角咧开一个令人作呕的弧度。
“啧,跑得倒是挺快,贱命一条,居然还没死。”他的声音粗嘎,如同砂纸摩擦,每一个字都淬着毒,“只可惜,爬到了这鸟不拉屎的鬼地方,扰了爷们的清净。”他的目光终于懒洋洋地转向我,像在打量一件碍眼的废物,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嘲弄,“怎么?就凭你这把老骨头,还想学人英雄救美?省省吧,把这小贱人交出来,爷心情好,赏你个痛快点的死法。”
他带来的黑衣杀手们堵在门口,如同沉默的礁石,冰冷的视线齐齐锁定了眼前看似文弱的男人。
刀疤脸的目光再次落到我身上,扫过我腰上的剑鞘,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有趣的事,那讥诮之意更浓,仿佛在看一只不自量力的蝼蚁:“‘无鞘剑’?呵,好大的名头!可惜啊,龟缩在这山沟里十年,怕是连剑都锈死了吧?识相的就赶紧滚开!溜得够快倒是可以留你一条命。”刀疤脸终究还是收住讥讽的语气,十年前江湖上的名头终究还是让他有了几分忌惮。
无鞘剑……这个沉寂了十年的名号,像一把生锈的钥匙,打开了沉重的过往。无数刀光剑影的画面碎片般闪过,带着沙沙铁锈的气味。指腹下意识地擦过腰间那空悬的剑鞘,冰冷的触感刺入骨髓。十年前,小妹死后,我曾找仇家复仇,杀了对方上下十口人,亲手折断佩剑,立下血誓,此生剑锋永藏,再不染江湖纷争。
竹榻上,那截褪色的红绳,在昏暗摇曳的油灯光线下,像一道尚未愈合的伤口。小妹临死前紧攥着红绳的手,与眼前女子昏迷中仍微微蜷缩的手指,在我混乱的视野中诡异地重叠。
十年枯坐,十年诵经,十年自欺欺人的“忘忧”……此刻,我应该立刻遁走,而不是在此处犹疑不定。
刀疤脸见我沉默,只当是惧怕,脸上狞笑更盛,竟向前一步,伸出布满老茧的手,直直抓向榻上昏迷的女子:“装聋作哑?那爷就亲手把这小娘皮拖出来,让你这老棺材瓤子开开眼……”
就在那只肮脏的手即将触碰到女子衣襟的刹那!
“唉……”
一声悠长的叹息,仿佛耗尽了全身的气力,又像是卸下了背负十年的枷锁,从我喉间逸出。叹息声落下的瞬间,我放下了手中滚烫的药罐。
炉火猛地一跳。
刀疤脸的手停在半空,他脸上的狞笑僵住,似乎没料到这声叹息蕴含的意味。
他没有看我。
右手抬起,探向茅屋角落那个蒙尘的角落。那里,倚墙靠着一根不起眼的黝黑木棍——那是我平日用来拨火的物件,顶端早已被烟火熏得焦黑。
手指握住那粗糙的木棍。
十年。整整十年我已不再握剑。
以为时光早已凝固,如同这蒙尘的剑鞘,如同山谷里沉默的磐石。
然而——
“铮——!”
一声清越到足以撕裂雨幕、洞穿灵魂的剑鸣,毫无预兆地在狭窄的茅屋中炸响,那不是金铁之声,却比任何利刃出鞘更加凛冽,那是是沉寂了三千六百个日夜的杀意,是深埋地底的熔岩终于冲破岩壳的咆哮。
一道刺目的、纯粹由意念凝聚的剑气,凭空自我握杵的右臂迸发而出,空气仿佛被无形的力量切割开,发出细微的嘶鸣。墙角蛛网寸寸断裂,屋顶的茅草簌簌落下湿重的灰尘。
刀疤脸脸上的狞笑彻底碎裂,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的惊骇!瞳孔骤然缩成针尖,那只伸出的手触电般缩回,身体本能地向后急退一步!
晚了。
就在他缩手后退的瞬间,就在那声剑鸣余音未绝的刹那——
我的目光,如同被那道无形剑气牵引,穿透混乱的空气,精准地钉在了刀疤脸因惊骇而后仰、衣领微微敞开的颈侧!
闪电再次划破屋外的黑暗,惨白的光透过破烂的窗棂,清晰地照亮了他脖颈裸露的皮肤。
那里,赫然刺着一个手掌大小的、青黑色的狰狞图案——一只展翅欲飞、爪牙毕露的夜枭!狠狠烙在我的眼底!
十年前,冲天烈焰,遍地尸骸……那个在火光中狞笑着割下父亲头颅的黑衣人首领,他颈后,正是这同样的夜枭刺青!是“鬼门十三煞”的标记!我心中恨意翻涌,原以为已经杀尽仇敌,却未曾料到,鬼门十三煞却在十年中又逐渐壮大,原来仇敌的爪牙,从未远离,它们蛰伏在黑暗里,终究还是循着血腥追来了。
凝固的时光,在这一刻轰然龟裂!此时刻骨恨意,如同决堤的洪流,瞬间冲垮了理智的堤坝,只剩下最原始、最暴烈的杀戮本能!我眼中泛红,如同烈焰。
“躲远些!”
一声低吼,不知是对榻上昏迷的女子,还是对十年前在血泊中断剑的自己。
话音未落,我已动了。
没有花哨的招式,没有多余的动作。握在手中的,依旧是那根黝黑的烧火棍。
然而,当它被灌注了沉寂的杀意时,它是与我一体的剑,手腕一振,剑气破空!
一道凝练到极致的乌光,带着撕裂一切的锐啸,直刺刀疤脸咽喉!速度之快,超越了肉眼捕捉的极限!空气被蛮横地排开,形成一道肉眼可见的、扭曲的轨迹!简陋的茅屋在这股沛然莫御的杀意冲击下,四壁的泥灰簌簌剥落,屋顶的茅草疯狂抖动,仿佛下一瞬就要被彻底掀飞!
刀疤脸脸上的惊骇瞬间化为恐惧,他怪叫一声,全身功力疯狂爆发,双臂交叉护在胸前,玄黑色的劲气汹涌而出,试图格挡这致命一击!
“噗!”
一声沉闷得令人牙酸的轻响。
乌光毫无阻滞地穿透了他仓促凝聚的护身罡气,如同热刀切过凝固的油脂。木棍的顶端,精准无比地没入了他交叉的双臂缝隙,点在了他的喉结之上。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被无限拉长。
刀疤脸脸上的恐惧凝固了。凸出的眼球死死盯着我,瞳孔深处映着我冰冷的脸,还有那根抵在他要害处的、普通的木棍。一丝难以置信的、混杂着无尽怨毒的绝望,在我眼中弥漫开来。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
“呃……”
一声短促而怪异的闷哼从他喉咙深处挤出。下一刻,他交叉护在胸前的双臂无力地垂下,整个身体如同被抽掉了脊梁骨,软软地向后倒去。后脑勺重重磕在冰冷的泥地上,发出“咚”的一声闷响。那双瞪大的眼睛里,生命的光彩迅速褪去,只剩下空洞的死灰。
头歪向一边,颈侧那只青黑色的夜枭刺青,在摇曳昏暗的灯光下,愈发显得狰狞可怖。
门口的黑衣杀手们,如同被无形的巨锤狠狠砸中,齐齐僵在原地!脸上的冷酷和残忍瞬间被无边的惊骇与恐惧所取代。枭的首领,那个在他们眼中如同凶神般的存在,竟然……死了?被这个看似文弱的中年男人,用一根烧火棍杀死?出手之快,甚至不能看清这个人的招式。
死寂。令人窒息的死寂笼罩了小小的茅屋。屋外的风声,更加狂暴地嘶吼着,风声席卷着大地,也把屋内弥漫开来的血腥污浊悉数卷走。
我缓缓站直身体,握着那根烧黑的木棍,那木棍上并没有血,甚至沾上的草木灰都未曾消失。杀意并未因刀疤脸的倒下而消散,反而如同实质的寒流,从我身上弥漫开来,席卷向门口那群僵立的黑衣人。
剑虽未出,剑意被唤醒,廿年用剑,无鞘剑虽断,但锋芒早就已经融入骨血。
今日,尘封的剑魂,终究如同蛰龙破阵。为了榻上那条无辜的性命,更为了那只夜枭刺青所代表的、十年前的血海深仇。
我的目光扫过门口那群惊骇欲绝的杀手,声音低沉,带着一种宣告死亡的寒意:
“下一个。”
门口那群黑衣杀手脸上的惊骇尚未散去,像一层冻结的灰白面具,死死焊在僵硬的皮肉上。刀疤脸扭曲的尸体就躺在泥地上,颈侧那只青黑色的夜枭刺青在摇曳灯影下狰狞依旧,暗红的血开始从喉间那个不起眼的孔洞里汩汩涌出,无声地渗入冰冷潮湿的泥地。
那血被泥土悉数吞进,他的木棍轻轻点地,轻得几乎被风声吞没,却像重锤狠狠擂在每一个黑衣杀手的心口,震得他们握着刀柄的手指关节一片惨白。
死寂只持续了一瞬。
“杀了他!剁碎了喂狗!”一个站在前排、身材精瘦、眼神如同淬毒冰棱的汉子猛地嘶吼起来,声音尖利扭曲,带着被彻底羞辱后的疯狂。他是刀疤脸的副手蝮蛇,颈侧同样刺着夜枭,盘踞在蜿蜒的旧疤上,更显阴鸷。“给老大报仇!上啊!”
吼声如同投入滚油的火星,瞬间点燃了恐惧催生的凶性。堵在门口的十数条黑影短暂地停滞后,骤然爆发出野兽般的嚎叫,刀光瞬间撕裂了屋内昏黄的油灯光晕,裹挟着浓烈的杀机和腥风,如同决堤的黑色浊流,狠狠撞向屋内!
刀锋劈开空气的厉啸刺耳欲聋。数道寒芒从不同角度刁钻地袭来,封死了我所有闪避的空间。目标不仅是我,更有我身后竹榻上昏迷不醒的女子!
我握着木棍的手腕纹丝未动。筋骨或许不再如巅峰时那般迅疾如电,但烙印在骨髓里的战斗本能被唤醒,那是无数次生死边缘锤炼出的直觉。
我没有后退,反而向前踏出半步!
木棍黝黑的影子在昏暗中划出一道几乎不可能捕捉的轨迹。没有惊天动地的声势,只有一种纯粹的、凝练到极致的“快”与“准”。它仿佛有了生命,循着最简洁致命的路径,精准无比地迎向那些撕裂空气的刀锋。
“铛!噗嗤!”
金石撞击的脆响与沉闷的撕裂声几乎同时炸开!
木棍的尖端如同拥有破罡之能,点在一柄劈砍而至的钢刀侧面最不受力的地方。持刀杀手只觉一股无可抗拒的螺旋巨力瞬间绞入手臂,虎口崩裂,钢刀脱手打着旋飞向屋顶,狠狠钉入一根粗大的房梁,尾柄兀自剧烈震颤!与此同时,木棍的侧面如同钝刀,带着一股摧枯拉朽的蛮横劲道,狠狠撞在另一名从侧面扑来、企图偷袭竹榻的杀手肋骨上!
“咔嚓!”
令人牙酸的骨裂声清晰可闻。那杀手连惨叫都未及发出,身体如同被重锤击中,口中鲜血狂喷,整个人向后倒飞出去,狠狠撞在身后的同伴身上,顿时滚作一团,将本就狭窄的门口堵得更死。
狭窄的茅屋瞬间成了修罗场。我的身影在刀光缝隙间游走,每一次拧身、跨步都精妙到极致,木棍在我手中化作一道致命的乌影。它或点、或砸、或崩、或扫,每一次出击都带着磅礴剑意,虽无剑之锋刃,却比任何利剑更令人胆寒。
噗!木棍捅穿了一个悍不畏死扑上来的杀手喉咙。
砰!沉重的杵身横扫,砸在另一个杀手太阳穴上,头颅瞬间凹陷下去。
闷响与惨嚎在狭小空间里疯狂回荡,每一次都伴随着生命的终结。浓烈的血腥气混合着潮湿的泥土和草药气息,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甜腥味道,几乎凝成实质。
蝮蛇那双毒蛇般的眼睛始终死死盯着我,并未贸然加入围攻。我如同潜伏在阴影里的毒虫,等待着猎物露出破绽的致命一击。眼见我在围攻下辗转腾挪,身形快如鬼魅,木棍每一次挥动都带走一条性命,蝮蛇脸上的肌肉剧烈抽搐,眼神中的怨毒几乎要滴出来。我猛地瞥见我为了格挡一记劈向竹榻的刀锋,身体有一个极其细微的、重心向左后侧倾斜的瞬间!
就是现在!
蝮蛇眼中凶光暴射!藏在袖中的右手闪电般甩出!没有刺耳的破空声,只有三道比风雨夜色更幽暗的乌光,无声无息地撕裂空气,成品字形射向我因格挡而暴露出的右肋空门!角度刁钻狠辣,时机拿捏得妙到巅峰!正是江湖中令人闻风丧胆的“蝮蛇三阴钉”!
我刚以木棍荡开身前的刀锋,一股冰冷刺骨的寒意已如跗骨之蛆般锁定了我的右肋!致命的警兆在脑中炸开!我瞳孔骤然收缩,身体本能地强行拧转,试图用最小的幅度避开要害。
嗤!嗤!
两声极其轻微、如同裂帛的声响。
一道乌光擦着我肋下的衣袍掠过,带起一片碎布。另一道却未能完全躲开,深深扎入了我左臂外侧的肌肉!一股尖锐冰冷的剧痛瞬间传来,伴随着诡异的麻痹感迅速蔓延!第三道乌光,被我强行扭身带起的木棍末端险之又险地磕飞,钉入泥墙,只留下一个深不见底的小孔。
左臂的力道瞬间泄去大半,伤口周围的皮肉肉眼可见地泛起一层不祥的青灰色!
“呃……”我闷哼一声,动作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丝迟滞。
就在这电光石火间,旧力已尽新力未生,一道快得只剩下残影的刀光,如同早已潜伏在侧的毒蛇,骤然从我视线的死角——右后侧、紧贴着竹榻边缘的阴影里暴起!刀锋无声无息,却带着灭绝一切的狠厉,直抹我因疼痛而微微暴露的脖颈。出刀者,正是蝮蛇!他甩出暗器的同时,早已如同鬼魅般无声无息地潜到了这个位置!
所有退路和防御动作都已被这前后夹击、阴毒到极点的连环杀招彻底封死!我甚至能清晰地看到蝮蛇眼中那即将得逞的、混合着残忍与狂喜的狞笑!
“啊——!!!”
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尖叫,骤然在我身后炸响!那声音充满了恐惧、痛苦的声音,尖利得足以刺穿耳膜!
尖叫来自竹榻!
一直昏迷的女子,不知何时竟被蚀骨针那万蚁噬骨般的剧痛生生折磨醒来!她身体蜷缩成一团,剧烈地抽搐着,那张苍白如纸的脸因痛苦而扭曲变形,冷汗和泪水混合着冲刷而下。在剧烈的挣扎中,她腕上那根褪色的红绳猛地绷紧,似乎被无意识的手指死死攥住、拉扯。
就在她尖叫抬头的瞬间,那双因剧痛而布满血丝、瞳孔都有些涣散的眼睛,猛地对上了蝮蛇那张布满阴狠杀意的脸!更准确地说,是死死盯住了蝮蛇因全力出刀而微微敞开的衣领下方——那颈侧蜿蜒旧疤之上,一只青黑色、爪牙狰狞的夜枭刺青,在昏暗摇曳的油灯光下,如同地狱爬出的印记,清晰地烙印在她的瞳孔深处!
“枭……!”女子喉咙里挤出破碎的音节,声音嘶哑变形,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血水里捞出来,没有恐惧,只有恨意,“是你们……是你们!!”极致的仇恨瞬间压倒了蚀骨针的剧痛,她不知从哪里爆发出一股可怕的力量,上半身猛地从竹榻上弹起,沾满血污的手指痉挛着拔出银簪,向前刺去,那疯狂而绝望的姿态,如同被逼到绝境的困兽。
蝮蛇全神贯注于那必杀的一刀,眼看刀锋就要触及我的皮肤,这突兀的、充满怨毒与疯狂的尖叫和扑刺的动作,如同平地惊雷,狠狠劈入他的心神!动作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丝极其细微的凝滞!那志在必得的刀锋,距离我的脖颈只差毫厘!
生死一线!
同类推荐
 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在哪看免费小说_已完结小说推荐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
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在哪看免费小说_已完结小说推荐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
花海棠
 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小说完整版_完结好看小说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
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小说完整版_完结好看小说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
花海棠
 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最新好看小说推荐_完本小说免费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
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最新好看小说推荐_完本小说免费双胞胎妹妹想代替我上名校(廖思思思思)
花海棠
 逐仙缘-Chapter90阉割和还债赵清热门免费小说大全_热门免费小说逐仙缘-Chapter90阉割和还债(赵清热门)
逐仙缘-Chapter90阉割和还债赵清热门免费小说大全_热门免费小说逐仙缘-Chapter90阉割和还债(赵清热门)
紫月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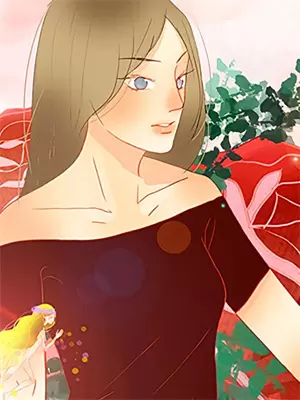 逐仙缘-Chapter89往日孽债颜仙李潇热门小说完结_热门的小说逐仙缘-Chapter89往日孽债颜仙李潇
逐仙缘-Chapter89往日孽债颜仙李潇热门小说完结_热门的小说逐仙缘-Chapter89往日孽债颜仙李潇
紫月月
 花子萧李玉之(逐仙缘-Chapter88颜言瑞之死)_《逐仙缘-Chapter88颜言瑞之死》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
花子萧李玉之(逐仙缘-Chapter88颜言瑞之死)_《逐仙缘-Chapter88颜言瑞之死》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
紫月月
 颜言瑞颜仙《逐仙缘-Chapter87花子萧的纠缠》完结版免费阅读_颜言瑞颜仙热门小说
颜言瑞颜仙《逐仙缘-Chapter87花子萧的纠缠》完结版免费阅读_颜言瑞颜仙热门小说
紫月月
 逐仙缘-Chapter86女皇的转世颜仙花子萧推荐完结小说_免费阅读逐仙缘-Chapter86女皇的转世(颜仙花子萧)
逐仙缘-Chapter86女皇的转世颜仙花子萧推荐完结小说_免费阅读逐仙缘-Chapter86女皇的转世(颜仙花子萧)
紫月月
 逐仙缘-Chapter85即将降生的孩子颜仙上官逾明_《逐仙缘-Chapter85即将降生的孩子》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
逐仙缘-Chapter85即将降生的孩子颜仙上官逾明_《逐仙缘-Chapter85即将降生的孩子》最新章节免费在线阅读
紫月月
 逐仙缘-Chapter84上官逾明我且看你能张狂到几时(赵清颜仙)完结的热门小说_全本免费完结小说逐仙缘-Chapter84上官逾明我且看你能张狂到几时(赵清颜仙)
逐仙缘-Chapter84上官逾明我且看你能张狂到几时(赵清颜仙)完结的热门小说_全本免费完结小说逐仙缘-Chapter84上官逾明我且看你能张狂到几时(赵清颜仙)
紫月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