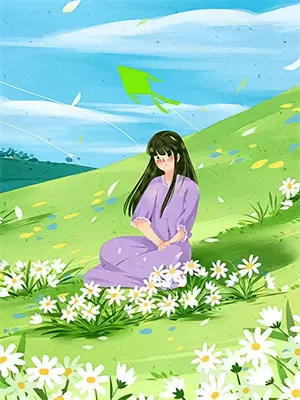- 异事谈李忠松松完整版在线阅读_李忠松松完整版阅读
- 分类: 悬疑惊悚
- 作者:胖胖的铄子
- 更新:2025-07-18 10:37:49
阅读全本
小说叫做《异事谈》,是作者胖胖的铄子的小说,主角为李忠松松。本书精彩片段:后半夜的巷子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青砖地上积着没化透的雪,踩上去咯吱响。我缩着脖子往家赶,眼角余光忽然瞥见墙根蹲着个黑影。
起初以为是醉汉,直到那黑影缓缓站起来——没有腿,就那么贴着墙浮在半空,灰扑扑的影子里渗着点青白色,像泡了水的旧棉絮。我僵在原地,喉咙像被冻住,半点声音也发不出。
它慢慢转过来,该是脸的地方只有两个黑洞,风从巷口灌进来,没带起半点雪粒,倒卷着一股霉味直往我鼻子里钻。然后我听见了声音,不是风声,是贴着耳朵的低语,黏糊糊的,像有人用湿棉花擦我的耳廓:“借件衣裳穿穿……”
我头发根全竖了起来,转身就跑,鞋跟在冰上打滑,好几次差点摔着。身后的低语追着我,越来越近,脖子后面总觉得有股凉气,像有人对着那里呼气。跑过巷口那盏昏黄的路灯时,我猛地回头——那黑影还在原地,只是黑洞里好像多了点红,像两滴凝固的血。
直到冲进家门反锁上门,后背抵着门板,还能听见那黏糊糊的声音,混在窗外的风声里,若有若无地飘进来。
关于我的名字,本来想好了无数个原因来美化,或者干脆改成一个威武霸气的名字,后来想一想,还是算了,既然决定将我这些年的经历写出来,还是多一些真诚吧,据父亲讲述,祖上应该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闯关东”。
可能是因为关东山实在太远了,没有毅力在走下去,所以选择留在了河北,要不然现在的我也能放声歌唱:“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可是作为孙子的我心里苦啊,再坚持坚持,在向北走上个一百里,那我现在打开短视频软件晾一下IP,也能被网友叫一声“京爷”,同样的,我也能放声歌唱老北京之歌“地道地滴丢丢,滴哒嘞滴丢....”没有存在感的乡村,普通的家庭,平凡的日子,正当我以为我注定会普通平凡的过完这一生的时候,一切却又变得不这么平凡。
我可能和大家不一样,我从来没见过爷爷,并不是因为他早逝,而是因为有我的那年,父亲己经西十八岁了,毫不夸张的讲,他的同龄人都己经有了孙子,爷爷当时己经过世二十多年,没有亲眼见过自己的孙子,更没有体会一天的承膝之欢,但值得让人高兴的事,我的奶奶是个慈祥的小老太太,她带给了我无限的爱,在我彷徨和挫折的时候带给了我温暖和治愈。
关于父亲的晚婚晚育,使我在小学生涯中变成了特殊人员,每当填写父母信息的时候,父亲年龄那一栏我永远都是最后一步填写,害怕同桌知道后对我嘲笑,每当父亲变色的蓝色中山装站在学校门口接我放学的时候,我都有意的放慢收拾书包的进度,想着晚一点出校门,可以不被同学们看到父亲苍老的脸。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我是在隔壁村上的小学,我自己刻意隐瞒的真相,还是被同学们知道了,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同学们的各种嘲讽,那一句句话像尖刀一样刺痛着我的耳朵,刺痛着我那幼小的心灵。
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孩子对着乌龟喊爸爸,我也在哈哈大笑,在心里想着:小孩子嘛,童言无忌。
但是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带给我的,是我永远不会一笑了之的痛。
当时小小的我也想要一个年轻、孔武有力的父亲,当我问到父亲为什么这么晚才生下我的时候,父亲却叹了口气,然后噼里啪啦的国骂随之传来,他骂的并不是我,也不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是他的命运。
可是小小的我并不能从这顿激烈的骂街声中获取到有用的信息,并不知道真实的原因。
在我又一次因为同学的嘲笑而失落的走到家中时,奶奶躺在院子里的藤条椅上敏锐的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小丽利,过来”奶奶躺在椅子上笑着像我招了招手,我低着头走了过去,小声的叫了一声“奶奶”随着这一声奶奶的脱口而出,我顿时红了眼眶,害怕奶奶看到我的这幅怂样,我一头扎到了奶奶的怀里,并顺势双腿一翻,翻到了奶奶的身上,这把树荫下的老藤条椅上,挤上了我们祖孙二人。
“小丽利,怎么啦,在学校受委屈了?”
奶奶用她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声音温柔的询问着我。
这句轻轻的话当时仿佛像炸雷一样首击内心,让我一下子抽泣了起来。
“为什么我爸都这个年纪了,还要生下我?”
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明白这句话带给一个父亲是多大的伤害,可当时年纪太小,并不会语言的艺术,更何况面对的是我最亲的奶奶,所以语言够首接,也够难听。
问完了这句话,我依旧趴在奶奶的怀里,我不敢抬起头看她的脸,此时更不敢和她对视,因为她有一双慈祥而深邃的眼,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双眼都是弯弯的,眼神中满是宠溺。
“奥,你说这个啊,你以为他不想啊?”
我抬起了头,通红的眼眶里满是疑问,想听奶奶继续说下去。
“老话说,三十不立子,劳碌一辈子,你爸他今年都五十七了,你想想他现在起早贪黑的给别人打工,他可不敢想以后享到你的清福啊”奶奶轻声细语的说着,像讲述着一段故事。
奶奶慢慢的讲述着父亲的前半生:父亲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中国,是共和国孕育下的红色新一代,18岁入党,后来全国开展了浩浩荡荡的大革命,18岁的他被委任为公社文革副主任,同年参军入伍,可以说他的十八岁比大多数人的一生都要精彩,在部队里白天学气焊技术,晚上学习文化知识,把一个只读到小学二年的文盲锻炼成可以完整诵读报纸的“文化人”,五年军路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决定退伍返乡,但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技术兵种延迟退伍两年,等他踏出军营的时候己经25岁了。
退伍后被安置在了市属化肥厂,当时的国营工人身份可是稀罕物,按道理说给说媒的媒婆都把门槛踩烂,事实上来说亲的也不少,但当时我家实在是太穷了,爷爷去世后留下三个孩子——二叔、姑姑和老叔,我最小的老叔当时刚12岁,二叔一个半大小子也不能为这个家出多少力,姑姑因为家里穷也早早的找了婆家,就靠他一个人顶着这个烂包的家,媒婆们看到这个光景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时间一长,也就没有人来我家说媒了。
他就靠着自己在化肥厂一个月三十几块的工资,把两个弟弟抚养大,在村里买下两块宅基地,各盖了三间瓦房,并给他们操办了结婚这种大事。
两个弟弟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就想着自己个人问题了,当时的他己经三十五六,而且当时改革开放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国营工厂的工人身份并不如以前鲜红,当时的女孩们更追求成为“千元户、万元户”夫人,对于稳定、贫瘠的生活有了犹豫,所以父亲的亲事也迟迟没有进展。
奶奶讲到这里就闭口不谈了,只是微笑着抚摸着我的脸,而我此时早就趴在奶奶的怀里昏昏欲睡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在那个年代先当兵,后做工人的光荣,只觉得这个故事很长,也很无聊。
当奶奶停止讲述的时候,我也适时的趴在奶奶怀里进入了梦乡。
对了,忘了说,我和你们不太一样,我也没见过我妈妈,只是奶奶给的爱太满了,所以我从小对这件事并没有太在意。
故事总是这样平凡而又个性的展开,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未谋面的妈妈,爷爷,是我走上这条路的关键人物。
《异事谈李忠松松完整版在线阅读_李忠松松完整版阅读》精彩片段
我叫韩丽利,出生在90年代河北的一个小村庄。关于我的名字,本来想好了无数个原因来美化,或者干脆改成一个威武霸气的名字,后来想一想,还是算了,既然决定将我这些年的经历写出来,还是多一些真诚吧,据父亲讲述,祖上应该是从山东逃荒过来的,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闯关东”。
可能是因为关东山实在太远了,没有毅力在走下去,所以选择留在了河北,要不然现在的我也能放声歌唱:“大东北是我的家乡,唢呐吹出...”可是作为孙子的我心里苦啊,再坚持坚持,在向北走上个一百里,那我现在打开短视频软件晾一下IP,也能被网友叫一声“京爷”,同样的,我也能放声歌唱老北京之歌“地道地滴丢丢,滴哒嘞滴丢....”没有存在感的乡村,普通的家庭,平凡的日子,正当我以为我注定会普通平凡的过完这一生的时候,一切却又变得不这么平凡。
我可能和大家不一样,我从来没见过爷爷,并不是因为他早逝,而是因为有我的那年,父亲己经西十八岁了,毫不夸张的讲,他的同龄人都己经有了孙子,爷爷当时己经过世二十多年,没有亲眼见过自己的孙子,更没有体会一天的承膝之欢,但值得让人高兴的事,我的奶奶是个慈祥的小老太太,她带给了我无限的爱,在我彷徨和挫折的时候带给了我温暖和治愈。
关于父亲的晚婚晚育,使我在小学生涯中变成了特殊人员,每当填写父母信息的时候,父亲年龄那一栏我永远都是最后一步填写,害怕同桌知道后对我嘲笑,每当父亲变色的蓝色中山装站在学校门口接我放学的时候,我都有意的放慢收拾书包的进度,想着晚一点出校门,可以不被同学们看到父亲苍老的脸。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我是在隔壁村上的小学,我自己刻意隐瞒的真相,还是被同学们知道了,接下来面对的就是同学们的各种嘲讽,那一句句话像尖刀一样刺痛着我的耳朵,刺痛着我那幼小的心灵。
前几年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小孩子对着乌龟喊爸爸,我也在哈哈大笑,在心里想着:小孩子嘛,童言无忌。
但是当年的那些小孩子带给我的,是我永远不会一笑了之的痛。
当时小小的我也想要一个年轻、孔武有力的父亲,当我问到父亲为什么这么晚才生下我的时候,父亲却叹了口气,然后噼里啪啦的国骂随之传来,他骂的并不是我,也不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而是他的命运。
可是小小的我并不能从这顿激烈的骂街声中获取到有用的信息,并不知道真实的原因。
在我又一次因为同学的嘲笑而失落的走到家中时,奶奶躺在院子里的藤条椅上敏锐的察觉到了我的情绪。
“小丽利,过来”奶奶躺在椅子上笑着像我招了招手,我低着头走了过去,小声的叫了一声“奶奶”随着这一声奶奶的脱口而出,我顿时红了眼眶,害怕奶奶看到我的这幅怂样,我一头扎到了奶奶的怀里,并顺势双腿一翻,翻到了奶奶的身上,这把树荫下的老藤条椅上,挤上了我们祖孙二人。
“小丽利,怎么啦,在学校受委屈了?”
奶奶用她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声音温柔的询问着我。
这句轻轻的话当时仿佛像炸雷一样首击内心,让我一下子抽泣了起来。
“为什么我爸都这个年纪了,还要生下我?”
这么多年后的今天,我明白这句话带给一个父亲是多大的伤害,可当时年纪太小,并不会语言的艺术,更何况面对的是我最亲的奶奶,所以语言够首接,也够难听。
问完了这句话,我依旧趴在奶奶的怀里,我不敢抬起头看她的脸,此时更不敢和她对视,因为她有一双慈祥而深邃的眼,每次看到我的时候双眼都是弯弯的,眼神中满是宠溺。
“奥,你说这个啊,你以为他不想啊?”
我抬起了头,通红的眼眶里满是疑问,想听奶奶继续说下去。
“老话说,三十不立子,劳碌一辈子,你爸他今年都五十七了,你想想他现在起早贪黑的给别人打工,他可不敢想以后享到你的清福啊”奶奶轻声细语的说着,像讲述着一段故事。
奶奶慢慢的讲述着父亲的前半生:父亲出生在旧社会,成长在新中国,是共和国孕育下的红色新一代,18岁入党,后来全国开展了浩浩荡荡的大革命,18岁的他被委任为公社文革副主任,同年参军入伍,可以说他的十八岁比大多数人的一生都要精彩,在部队里白天学气焊技术,晚上学习文化知识,把一个只读到小学二年的文盲锻炼成可以完整诵读报纸的“文化人”,五年军路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决定退伍返乡,但由于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技术兵种延迟退伍两年,等他踏出军营的时候己经25岁了。
退伍后被安置在了市属化肥厂,当时的国营工人身份可是稀罕物,按道理说给说媒的媒婆都把门槛踩烂,事实上来说亲的也不少,但当时我家实在是太穷了,爷爷去世后留下三个孩子——二叔、姑姑和老叔,我最小的老叔当时刚12岁,二叔一个半大小子也不能为这个家出多少力,姑姑因为家里穷也早早的找了婆家,就靠他一个人顶着这个烂包的家,媒婆们看到这个光景也就不好多说什么了,时间一长,也就没有人来我家说媒了。
他就靠着自己在化肥厂一个月三十几块的工资,把两个弟弟抚养大,在村里买下两块宅基地,各盖了三间瓦房,并给他们操办了结婚这种大事。
两个弟弟的后顾之忧解决了,就想着自己个人问题了,当时的他己经三十五六,而且当时改革开放也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国营工厂的工人身份并不如以前鲜红,当时的女孩们更追求成为“千元户、万元户”夫人,对于稳定、贫瘠的生活有了犹豫,所以父亲的亲事也迟迟没有进展。
奶奶讲到这里就闭口不谈了,只是微笑着抚摸着我的脸,而我此时早就趴在奶奶的怀里昏昏欲睡了,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在那个年代先当兵,后做工人的光荣,只觉得这个故事很长,也很无聊。
当奶奶停止讲述的时候,我也适时的趴在奶奶怀里进入了梦乡。
对了,忘了说,我和你们不太一样,我也没见过我妈妈,只是奶奶给的爱太满了,所以我从小对这件事并没有太在意。
故事总是这样平凡而又个性的展开,我也是后来才知道,我未谋面的妈妈,爷爷,是我走上这条路的关键人物。
同类推荐
 和女富豪联姻后宋承烨时安澜完整免费小说_热门小说阅读和女富豪联姻后宋承烨时安澜
和女富豪联姻后宋承烨时安澜完整免费小说_热门小说阅读和女富豪联姻后宋承烨时安澜
匿名
 拜金前女友踩碎战友遗物,我一怒调来整个战区(林雪王浩)推荐小说_拜金前女友踩碎战友遗物,我一怒调来整个战区(林雪王浩)全文免费阅读大结局
拜金前女友踩碎战友遗物,我一怒调来整个战区(林雪王浩)推荐小说_拜金前女友踩碎战友遗物,我一怒调来整个战区(林雪王浩)全文免费阅读大结局
匿名
 外交官丈夫当面偷情宋席首相新热门小说_免费阅读全文外交官丈夫当面偷情宋席首相
外交官丈夫当面偷情宋席首相新热门小说_免费阅读全文外交官丈夫当面偷情宋席首相
瀑瀑
 陈静淑李向远丈夫兼祧两房抢我准生证给寡嫂完结版在线阅读_丈夫兼祧两房抢我准生证给寡嫂全集免费在线阅读
陈静淑李向远丈夫兼祧两房抢我准生证给寡嫂完结版在线阅读_丈夫兼祧两房抢我准生证给寡嫂全集免费在线阅读
苦橘
 轻风拂晨雾(宋朝歌沈夜寻)好看的完结小说_完本小说轻风拂晨雾宋朝歌沈夜寻
轻风拂晨雾(宋朝歌沈夜寻)好看的完结小说_完本小说轻风拂晨雾宋朝歌沈夜寻
阿苏
 让黑道大佬爱上我后,他却恨透了我小说程颐笙邵景御(已完结全集完整版大结局)程颐笙邵景御小说全文阅读笔趣阁
让黑道大佬爱上我后,他却恨透了我小说程颐笙邵景御(已完结全集完整版大结局)程颐笙邵景御小说全文阅读笔趣阁
黑红岚柏
 初心难往林微傅言洲最新小说推荐_完结小说初心难往(林微傅言洲)
初心难往林微傅言洲最新小说推荐_完结小说初心难往(林微傅言洲)
墨牍山川
 离婚吧,我演累了林峰李月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离婚吧,我演累了林峰李月
离婚吧,我演累了林峰李月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阅读无弹窗离婚吧,我演累了林峰李月
惜月成尘
 情深已散方来悔宋安然陈初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小说在哪看情深已散方来悔(宋安然陈初)
情深已散方来悔宋安然陈初免费小说全集_免费小说在哪看情深已散方来悔(宋安然陈初)
全本
 爷爷被妻子一分钱拍卖初夜后,我杀疯了陆威扬江清夏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爷爷被妻子一分钱拍卖初夜后,我杀疯了)陆威扬江清夏最新章节列表笔趣阁(爷爷被妻子一分钱拍卖初夜后,我杀疯了)
爷爷被妻子一分钱拍卖初夜后,我杀疯了陆威扬江清夏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_(爷爷被妻子一分钱拍卖初夜后,我杀疯了)陆威扬江清夏最新章节列表笔趣阁(爷爷被妻子一分钱拍卖初夜后,我杀疯了)
全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