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高温炼狱(冰冷林霄)在线阅读免费小说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高温炼狱(冰冷林霄)
- 分类: 其它小说
- 作者:虚构哲学家
- 更新:2025-07-16 18:02:04
《高温炼狱(冰冷林霄)在线阅读免费小说_完整版小说免费阅读高温炼狱(冰冷林霄)》精彩片段
重生回高温末世前三天,林霄卖房囤货抢占顶楼。当室外温度突破60℃时,
整栋楼的邻居开始死亡。“顶楼有空调!他囤了水!”绝望的人群疯狂砸门。隔着防盗门,
他认出领头的张大爷——昨天还笑着送他腊肠。老人中暑倒地瞬间,人群的嘶吼突然停止,
所有眼睛在热浪中灼烧。林霄慢慢拉上最后一道合金窗。
重活一世他终于明白:末日里最致命的不是高温,是人心。汗水。冰冷粘腻,
沿着额角蜿蜒爬行,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滑腻感,最终滴落在枕套上,
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林霄猛地睁开眼,胸腔像个破风箱般剧烈起伏,
每一次吸气都带着铁锈般的血腥味,灼热的气流仿佛还在灼烧着他的喉咙、肺部,
每一个细胞都在尖叫着干涸与撕裂。
眼前不是记忆深处那片被高温扭曲、泛着死白光芒的焦灼天空。
没有龟裂如同巨兽枯骨的大地,没有那无处不在、能将人烤成人干的恐怖热浪,
更没有散落在瓦砾间那些风干蜷缩、面目模糊的黑色物体。天花板上,
一盏有些年头的吸顶灯静静悬着,灯罩边缘积了层薄薄的灰。
阳光透过半旧的浅蓝色窗帘缝隙溜进来,在靠墙的书桌上投下一道明晃晃的光斑。空气里,
漂浮着小区楼下刚修剪过的青草气味,混合着昨夜残留的一点蚊香气息。平凡,安稳,
甚至带着点慵懒的夏日早晨气息。这巨大的反差像一柄冰冷的铁锤,狠狠砸在他的太阳穴上。
“不…不可能…” 他喉咙里挤出破碎的气音,挣扎着想坐起来,手臂却软得没有一丝力气,
只能徒劳地撑起一点上半身。视线慌乱地扫过房间。单人床,磨得发亮的书桌,
桌上那台积灰的旧笔记本电脑屏幕还固执地亮着,屏保图案是几只傻乎乎游动的热带鱼。
墙上,一张几年前买的廉价风景画,色彩俗艳。一切熟悉得令人心悸,又陌生得如同隔世。
他回来了。真的回来了!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猛地一缩,随即疯狂地擂动起来,
撞击着肋骨,发出沉闷的巨响,几乎要冲破胸膛。血液在血管里奔涌咆哮,
带着劫后余生的狂喜和深入骨髓的恐惧,瞬间冲上头顶,又狠狠坠回脚底。
他几乎是滚下床的,膝盖重重磕在冰冷的地板上,钻心的疼痛反而让他更清醒了一分。
他连滚爬爬扑向书桌,颤抖的手指狠狠戳向老旧鼠标的按键。屏幕上的热带鱼瞬间消失,
露出深蓝色的桌面背景。右下角,时间栏。2025年7月12日,
上午 7:23日期像烧红的烙铁,烫进他的瞳孔。三天!
距离那场席卷全球、将世界拖入炼狱的恐怖高温灾难降临,只剩下最后七十二小时!
嗡——大脑深处传来一阵尖锐的鸣响,视野边缘开始发黑。不是错觉!
他猛地抬起自己的左手小臂,目光死死钉在手肘内侧。那里,皮肤完好,
没有记忆中那个在高温下溃烂流脓、最终留下狰狞扭曲疤痕的伤口。但此刻,那片皮肤之下,
一种熟悉的、深入骨髓的灼痛感正在苏醒。它像一条苏醒的毒蛇,沿着神经纤维向上游走,
冰冷地提醒着他,那并非一场噩梦。那是烙进灵魂的印记,
是高温地狱在他身体里残留的余烬!每一次呼吸,每一次心跳,
都在唤醒那刻骨铭心的灼烧与干渴。“嗬…” 他喉咙里发出一声短促的抽气,
猛地从地上弹起,动作快得带倒了一把椅子,椅子腿摩擦地板发出刺耳的刮擦声。
他扑到窗边,一把扯开那碍眼的浅蓝色窗帘。窗外,阳光灿烂得有些刺眼。
楼下的小区花园绿意盎然,几个穿着清凉的老人慢悠悠地打着太极。远处,
城市的天际线在薄雾中清晰可见,车流在环线上汇成闪光的河流。世界运转如常,
充满了七月清晨的勃勃生机。然而,在林霄的视网膜上,
这鲜活的一切正被一层急速蔓延的、带着死亡气息的灰白所覆盖。
烟;那些悠闲的老人、路上匆忙的行人、车里吹着空调的乘客…他们会像被投入熔炉的蜡像,
在难以想象的高温中扭曲、倒下、碳化。空气不再流动,凝固成滚烫的、令人窒息的固体。
水成了比黄金更奢侈的传说。城市在死寂中沸腾,最终,只剩下废墟、焦尸,
以及幸存者眼中彻底熄灭的、比烈日更灼人的疯狂。末日,不是缓慢的侵蚀,
而是瞬间降临的焚化炉!“呼…呼…” 林霄扶着滚烫的窗框,剧烈地喘息,
额头抵在冰凉的玻璃上,试图汲取一丝冷静。汗珠顺着他的鼻尖滴落,砸在地板上,
晕开一小片深色。身体深处那源自灵魂的灼痛感还在隐隐作祟,像毒蛇的獠牙,
冰冷地抵着他的神经末梢。时间!他需要时间!三天,七十二小时,
每一秒都是向死神手里抢夺生机的筹码!钱!他需要大量的钱!
食物、水、药品、能源…所有能在高温地狱里硬生生凿出一条活路的物资,都需要钱!
大量的钱!目光如同鹰隼,猛地锁定在床头柜上那个半旧的深棕色皮质钱包上。他扑过去,
一把抓起,手指因为过度用力而指节发白。粗暴地翻开,
几张皱巴巴的百元钞票可怜地蜷缩在夹层里。几张银行卡,冰冷的塑料触感。
他抽出那张工资卡,指尖捏得发白。账户余额:三万七千六百五十二块八毛三。这点钱,
连塞末日堡垒的一个墙角缝都不够!绝望的冰水还没来得及浇透心脏,
一股更疯狂的念头已经像野火般燎原而起。他猛地抬起头,视线如同实质的探照灯,
扫过这间承载了他几年漂泊记忆、此刻却显得无比脆弱的小屋。墙壁有些发黄,
书桌边缘掉漆,床垫微微塌陷…这些微不足道的瑕疵,
此刻在他眼中却镀上了一层关乎生死存亡的奇异光泽。这房子!
这套位于城市边缘、不算新也不算大,但能为他换来一线生机的唯一不动产!“卖!
” 这个字眼像烧红的铁块从他齿缝间迸出,带着决绝的滚烫气息。没有一丝犹豫。
他抓起桌上那个屏幕已经布满蛛网般裂痕的手机,手指在冰凉的屏幕上划开通讯录。
指尖因为用力微微颤抖,悬停在那个标注着“黑心中介-王胖子”的名字上方。王胖子,
本地房产中介圈里有名的吸血鬼,手段狠辣,吃差价从不手软。搁在平时,
林霄绝对绕着他走。但现在?时间就是命!他需要现金,需要快!王胖子这种人的“效率”,
此刻成了唯一的救命稻草。电话拨通,只响了一声就被接起,仿佛对方就等在电话那头。
“喂?林老弟?稀客啊!怎么想起哥哥我了?” 王胖子油腻腻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
带着惯有的、令人不适的热情。林霄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冷静,
甚至带着点急迫的焦虑:“王哥,帮我个忙。城西那套小户型,急出!钥匙在门口地垫下面,
产权证在书桌左边第二个抽屉。价格,” 他顿了顿,心脏在胸腔里沉重地撞了一下,
几乎是咬着牙吐出那个数字,“低于市场价三成!但有一个条件——”“低于三成?!
” 王胖子夸张的惊呼打断了他,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难以置信的贪婪,
“老弟你……遇上事儿了?赌了?还是……嘿嘿?”“少废话!
” 林霄的声音陡然变得冰冷、强硬,像淬了火的刀锋,
隔着电话线都让那边的王胖子噎了一下,“全款!现金!今天!就今天必须到账!做不到,
我立刻找别家!”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令人窒息的沉默,只能听到王胖子粗重的呼吸声。
林霄能想象到那张油腻的胖脸上,小眼睛一定在飞速转动,
计算着这从天而降的巨大馅饼和他能从中榨取多少油水。几秒钟后,
王胖子那特有的、仿佛粘着蜜糖又藏着刀子的声音再次响起,语速快得惊人:“行!
林老弟爽快!哥哥我豁出去了!你等着!最多……最多下午三点!三点前,钱一定到你账上!
合同我马上带人过去签!钥匙是吧?书桌抽屉?放心!包在我身上!” 他拍着胸脯保证,
声音里是压抑不住的狂喜。“嘟…嘟…嘟…”林霄没再废话,直接挂断了电话。
手机被他随手扔在床上,发出沉闷的一声。他背靠着冰冷的墙壁,缓缓滑坐在地板上,
汗水已经浸透了单薄的T恤,紧紧贴在皮肤上,带来一阵黏腻的凉意。
身体里那条毒蛇般的灼痛感似乎蛰伏了一些,但心脏仍在胸腔里疯狂擂动,
震得耳膜嗡嗡作响。成了。第一步,最疯狂、最孤注一掷的一步,迈出去了。
用安身立命的窝,去赌一个在末日里活下去的可能。他闭上眼,
象再次清晰地浮现——龟裂的大地、扭曲的空气、风干的尸体……“不够…” 他喃喃自语,
猛地睁开眼,目光锐利如刀。卖房的钱只是地基,他需要在这地基上,用最快的速度,
垒起一座足以对抗地狱烈火的堡垒!他需要据点!一个易守难攻、拥有潜在资源的据点!
记忆的碎片在灼热的脑海中飞速拼凑。顶楼!他租住的这栋老式居民楼的顶楼!
那里有一套空置已久、据说因为漏水问题一直租不出去的房子!最关键的是,老楼的设计,
巨大的储水箱就在顶楼天台!那是灾难初期,在市政供水彻底崩溃前,
距离最近、最有可能被忽视的生命之源!还有天台!开阔的空间,
是安装太阳能板的绝佳位置!在电力成为奢侈品的末日里,
那将是维持最后一点“文明”的命脉!念头一起,身体便像上了发条。林霄猛地从地上弹起,
冲向房门。钥匙插进锁孔,拧动,拉开——“哟,小林?今天这么早?
” 一个熟悉而和蔼的声音在楼道里响起。林霄的动作瞬间僵住。
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攥紧,狠狠一缩。他缓缓抬起头。斜对门,602室的门开着。
张大爷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汗衫,手里拎着个垃圾袋,正笑呵呵地看着他。
老人脸上深刻的皱纹里都堆满了慈祥,花白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眼神温和,
像看着自家子侄。“嗯…有点事,张大爷。” 林霄的喉咙有些发干,
声音带着连他自己都未察觉的紧绷。
他的目光下意识地扫过张大爷布满老年斑、却显得异常温暖的手。
就是这双手…在记忆碎片里,在人群疯狂冲击防盗门、发出野兽般嘶吼的最前端,
死死抠抓着冰冷的金属门框,指甲崩裂,留下暗红的血痕…那张布满皱纹的脸,
在极度高温和绝望下扭曲得如同恶鬼,
浑浊的眼睛里燃烧着要将他生吞活剥的疯狂…“年轻人忙点好!忙点有奔头!
” 张大爷没察觉林霄瞬间的异样,依旧笑呵呵的,语气里满是长辈的关怀,“对了,小林,
家里做了点腊肠,刚晾好,味儿正!你一个人住,做饭不方便,待会儿给你拿点尝尝!
”腊肠…林霄胃里猛地一阵翻搅,强烈的恶心感直冲喉咙。记忆里,在高温蒸煮下,
那些曾经散发着诱人香气的腊肠,迅速腐败变质,散发出令人作呕的甜腻腥臭,
招来了密密麻麻、挥之不去的绿头苍蝇…而那时,一块干净的面包,一口清水,
都足以引发一场血腥的争夺。“不…不用了,张大爷,谢谢您。
” 林霄几乎是咬着牙才挤出这句话,每一个字都带着冰碴子。他猛地低下头,
不敢再看老人那关切的脸,侧身快速从张大爷身边挤过,逃也似地冲下楼梯,
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里回荡得异常急促。身后,
似乎还隐约传来张大爷带着点不解的嘟囔:“这孩子…今天咋毛毛躁躁的…”那和蔼的声音,
此刻却像针一样扎在林霄的耳朵里。他冲出单元门,
七月的热浪混合着汽车尾气和行道树的气息扑面而来。他站在明晃晃的阳光下,大口喘息着,
像一条离水的鱼。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撞击,不是因为奔跑,而是因为刚才那短暂的对视。
那张慈祥的脸与记忆中狰狞扭曲的面孔重叠在一起,形成一种尖锐而恐怖的割裂感。
身体深处,那条蛰伏的灼痛之蛇仿佛又抬起了头,冰冷的信子舔舐着他的神经。
他用力甩了甩头,试图将那张脸、那个声音从脑海里驱逐出去。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目标明确:顶楼!林霄像一阵裹挟着沙砾的风,
冲进小区物业那间弥漫着灰尘和旧纸张气味的办公室。
面对那个睡眼惺忪、一脸不耐烦的秃顶中年物业经理,他没有任何迂回,
直接将一沓刚从ATM机里取出的、还带着油墨味的现金拍在掉漆的木质桌面上。“701,
顶楼那套空房,” 林霄的声音斩钉截铁,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租三个月,押一付一。
现金,现在签。”经理被那沓钱和对方眼中近乎凶狠的急切惊得瞌睡全无,
小眼睛在钞票和林霄紧绷的脸上来回扫视,浑浊的眼珠里闪过一丝精明的算计:“701?
那套…小林啊,不是我不租给你,那房子漏得厉害!夏天太阳一晒,屋里跟蒸笼似的,
冬天又灌风,水管也老化了,时不时就…”“我知道。” 林霄打断他,声音冰冷,
“就它了。合同,钥匙,现在就要。” 他又从裤兜里摸出几张百元钞票,
压在原先那沓钱上,动作干脆利落,“这是今天的‘辛苦费’。”经理喉结滚动了一下,
贪婪的目光黏在钞票上,脸上的为难瞬间被一种油腻的谄笑取代:“哎呀,你看你这小伙子,
急脾气!行行行,既然你非要租,我也不好拦着不是?合同…合同马上就好!钥匙就在这!
” 他肥胖的手以与体型不符的敏捷,飞快地拉开抽屉,
翻出钥匙和一式两份的制式租房合同,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声响。钥匙入手,
带着金属特有的冰凉和粗糙的锈迹感。林霄抓起属于自己的那份合同,
看都没看那还在絮叨着“有问题随时找我”的经理,转身就走。时间,每一秒都在燃烧!
他冲回自己所住的403室。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破釜沉舟的寂静。他打开衣柜,
只拿出一个结实耐用的双肩背包,动作快得近乎粗暴。几件耐磨的深色T恤、长裤,
几双厚袜子,洗漱包里塞进牙刷牙膏毛巾,动作没有丝毫拖泥带水。最后,
他的目光落在书桌抽屉里那个老旧的铁盒上。打开铁盒,
里面静静地躺着几样东西:一把刃口磨得雪亮的多功能瑞士军刀,
冰冷的金属光泽映着他沉静的眼;一个防风打火机,
塑料外壳有些磨损;还有一本翻得卷了边的《野外生存手册》。
这些都是他以前户外徒步时的“玩具”,此刻却成了末日求生清单上的关键物品。
他拿起军刀,指腹感受着那熟悉的、令人心安的锋利触感,
然后毫不犹豫地将它们全部塞进背包夹层。拉上背包拉链,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他最后环顾了一眼这个住了几年的小屋。书桌、床、墙上的画……平凡生活的痕迹,
很快就会被高温抹去。没有留恋,只有一种剥离过去的决绝。他背上包,拉开门,
头也不回地走向楼梯。脚步踩在水泥台阶上,发出沉重而急促的回音,一层,两层,
三层……空气似乎都因他周身散发出的紧迫感而凝滞。七楼。701室的铁门紧闭,
门锁孔有些锈蚀。他插入钥匙,用力拧动,锁芯发出艰涩的“咔哒”声。
一股混合着浓重灰尘、霉菌和淡淡石灰粉味道的闷热气息扑面而来。房间不大,
标准的一室一厅。墙壁斑驳,大片大片的墙皮因渗水而剥落、发黄,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
天花板角落,几道深褐色的水渍蜿蜒而下,像丑陋的伤疤。窗户是老式的单层玻璃,
此刻紧闭着,室内闷热得像个桑拿房,汗水瞬间就从林霄的额角、脖颈渗了出来。
但他毫不在意。他的目光锐利如鹰隼,快速扫过房间结构——承重墙的位置,门窗的朝向。
客厅和卧室的窗户都朝南,正对着毫无遮挡的炽烈阳光。很好,这正是他需要的!阳光,
在末日里,将是驱动希望的能源!
他的视线最终定格在客厅与卧室之间那堵不算厚的隔断墙上。
一个计划在灼热的脑海中瞬间成型。第一步,加固!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壳!
手机再次震动,屏幕亮起。
:您尾号XXXX账户7月12日13:47收入人民币 3,880,000.00元,
余额……卖房款!到账了!比王胖子承诺的下午三点还早!时间!钱!两样最关键的要素,
终于在这一刻握在了掌心!林霄没有丝毫停顿,手指在手机屏幕上快得几乎出现残影。
世偶然接触而深深刻在记忆里的号码——一个专门承接各种“特殊要求”装修工程的小工头,
老陈。电话接通,背景音嘈杂混乱。“喂?谁?
” 一个粗哑的、带着浓重地方口音的声音响起,伴随着金属碰撞的噪音。“陈老板?
有急活,大活,现金结。” 林霄的声音冷静得可怕,直奔主题,“地点发你。
要求:最高规格断桥铝门窗,双层加厚防爆玻璃,今天下午五点前必须送到!防盗门,
银行金库同级别!另外,需要一支至少十人的队伍,工钱双倍!现在就开工!干不干?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五秒,只有粗重的呼吸声。显然,
这种时间紧、要求高到离谱、但报酬异常丰厚的“急活”,超出了老陈的日常经验。
“……活没问题!钱到位,人我给你拉来!门窗五点前到不了,四点!四点我亲自押车送到!
防盗门…金库级有点难,但我认识人!有现货!加急!” 老陈的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一种被巨额利润刺激的亢奋和赌徒般的狠劲,“工人我马上叫!工钱双倍?老板爽快!
地址发我!现在就动!”“地址马上发你。记住,四点,东西和人,必须到。晚一分钟,
钱减半。” 林霄冷冷地撂下最后一句警告,挂断电话,迅速将701的定位发了过去。
他不需要温情脉脉的讨价还价,末日倒计时的秒针在他脑中滴答作响,震耳欲聋。
他只需要效率,以及用金钱砸出来的、不容置疑的服从。老陈,和他手下那群只认钱的工人,
是最快的刀。做完这一切,林霄片刻不停,转身冲出701室,
沉重的防盗门在他身后“砰”地一声撞上,激起一片灰尘。他三步并作两步冲下楼梯,
冲出单元门,灼热的空气瞬间包裹全身。小区门口,
一辆车身布满泥点、破旧不堪的黄色出租车刚好停下。他拉开车门,像一阵风般钻了进去。
“师傅,最近的建材批发市场!快!” 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急促。
司机是个沉默的中年汉子,透过后视镜看了一眼后座乘客紧绷的脸色和额角滚落的汗珠,
没多问一个字,猛地一踩油门。破旧的发动机发出一声嘶吼,车子像离弦的箭般蹿了出去,
汇入车流。批发市场巨大的彩钢棚顶在烈日下反射着刺眼的白光,
空气里混杂着水泥、木材、塑料和金属的气味。林霄如同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目标明确,
脚步生风。“老板,加厚隔热棉!最好的!阻燃等级最高那种!有多少要多少!
仓库地址给我,现在装车送!” 他拍着保温材料店的柜台,语速快得像扫射的子弹。
“铝箔隔热板?整卷的?十卷?马上要?行!马上装!
” 板材区的老板看着手机里瞬间到账的定金,眼睛发亮,吆喝着工人立刻动手。
“静音发电机?最大功率的柴油机?两台!对,现在就要现货!配套的柴油桶,给我装满!
二十桶!送到这个地址!” 他在震耳欲聋的机电区穿梭,声音盖过机器的轰鸣。“纯净水?
桶装的?一百桶?瓶装矿泉水?两百箱?食品?压缩饼干、肉罐头、真空大米?维生素片?
消炎药?抗生素?纱布?酒精?有多少搬多少!” 在食品和医药批发区域,
他近乎扫荡的采购清单和毫不迟疑的支付方式,让几个老板目瞪口呆,随即爆发出狂喜,
指挥着搬运工如同蚂蚁搬家般将堆积如山的物资装上他临时高价雇来的几辆小货车。
汗水早已浸透了他的衣衫,紧贴在皮肤上,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灼热的铁锈味。
身体深处那条象征前世灼伤的毒蛇又开始不安地游动,带来阵阵尖锐的幻痛,像是在催促,
又像是在警告。他强迫自己忽略,大脑高速运转,核对清单,指挥装车,付款转账,
动作精准得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钱如流水般泼洒出去,换来的,
是堆满一辆辆货车的、在阳光下闪烁着冰冷或包装光泽的生存物资。
当他带着最后一车满满的瓶装水和药品,如同一位押送着帝国最后宝藏的疲惫将军,
终于返回那个老旧的小区时,时间已经指向了下午三点四十分。
夕阳的余晖将天空染成一片燥热的橘红,空气闷热粘稠,没有一丝风。小区门口,
景象已截然不同。
几辆沾满泥浆、车身印着模糊不清装修广告的面包车和小货车粗暴地停在楼前狭窄的空地上,
几乎堵住了道路。七八个光着膀子、皮肤黝黑、肌肉虬结的汉子正吆喝着,
车上卸下巨大的、闪烁着崭新金属冷光的断桥铝窗框和厚厚的、泛着幽蓝光泽的防爆玻璃板。
沉重的金属部件砸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巨响。旁边,
另外几个工人正小心翼翼地挪动着一扇看起来厚重得惊人的深灰色金属门板。
那门板表面布满复杂的锁具和加固结构,泛着冷硬的、近乎于装甲的光泽,
正是他要求的“金库级”防盗门。领头的是个矮壮敦实、穿着沾满油污迷彩裤的男人,
四十多岁,一脸横肉,脖子上挂着条小指粗的金链子。正是工头老陈。他挥舞着粗壮的胳膊,
唾沫横飞地指挥着,声音洪亮而粗鲁:“快!快!都他妈没吃饭啊!窗框!那边!小心玻璃!
操!说你呢!那门重!四个人抬!对!轻点!磕坏了老子扒你皮!
” 他眼角的余光瞥见林霄和他身后跟着的、装满物资的货车,立刻小跑着迎了上来,
油腻的脸上挤出混合着讨好和邀功的笑容。“老板!您看!按您要求,最好的料!四点前,
准时到!” 他指着那些正在卸下的门窗,“兄弟们手底下有数,今晚通宵,
保管给您把这‘壳’弄得比王八盖子还硬实!” 他拍着胸脯保证,
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瞟向林霄身后货车上那些堆积如山的物资,
小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疑和贪婪。林霄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同类推荐
 丈夫的女秘书罚我做保洁后,工厂完了朱明明郑合免费小说在线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丈夫的女秘书罚我做保洁后,工厂完了(朱明明郑合)
丈夫的女秘书罚我做保洁后,工厂完了朱明明郑合免费小说在线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丈夫的女秘书罚我做保洁后,工厂完了(朱明明郑合)
玖日故事
 亲爹祭天,她沉重的爱我不要了陆涛苏青好看的小说推荐完结_在哪看免费小说亲爹祭天,她沉重的爱我不要了陆涛苏青
亲爹祭天,她沉重的爱我不要了陆涛苏青好看的小说推荐完结_在哪看免费小说亲爹祭天,她沉重的爱我不要了陆涛苏青
玖日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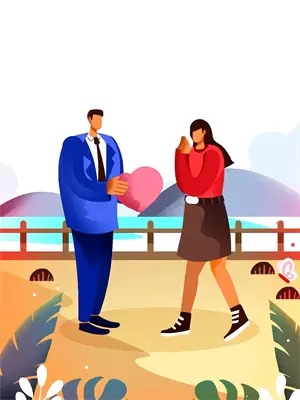 婆婆选我死后发现我才是亲生的(周润言林秀玉)免费完结小说_免费小说在线阅读婆婆选我死后发现我才是亲生的(周润言林秀玉)
婆婆选我死后发现我才是亲生的(周润言林秀玉)免费完结小说_免费小说在线阅读婆婆选我死后发现我才是亲生的(周润言林秀玉)
玖日故事
 儿子毕业旅行被困沙漠沈心柔陆景山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儿子毕业旅行被困沙漠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儿子毕业旅行被困沙漠沈心柔陆景山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儿子毕业旅行被困沙漠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玖日故事
 用黑卡请舍友吃饭,我倒欠一个亿(柳萌萌朱炎)热门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用黑卡请舍友吃饭,我倒欠一个亿(柳萌萌朱炎)
用黑卡请舍友吃饭,我倒欠一个亿(柳萌萌朱炎)热门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用黑卡请舍友吃饭,我倒欠一个亿(柳萌萌朱炎)
玖日故事
 我把信用卡刷爆后,想整容的表姐疯了江川乔念安热门的小说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我把信用卡刷爆后,想整容的表姐疯了江川乔念安
我把信用卡刷爆后,想整容的表姐疯了江川乔念安热门的小说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我把信用卡刷爆后,想整容的表姐疯了江川乔念安
玖日故事
 重生后我为三皇子驭灵成兵(驭灵顾逸川)网络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重生后我为三皇子驭灵成兵(驭灵顾逸川)
重生后我为三皇子驭灵成兵(驭灵顾逸川)网络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重生后我为三皇子驭灵成兵(驭灵顾逸川)
玖日故事
 身为貔貅的我不再替老公转运宋晩绮谢归舟完整免费小说_热门小说阅读身为貔貅的我不再替老公转运宋晩绮谢归舟
身为貔貅的我不再替老公转运宋晩绮谢归舟完整免费小说_热门小说阅读身为貔貅的我不再替老公转运宋晩绮谢归舟
玖日故事
 下乡被男友造黄谣,我勾上糙汉(周清泽沈云海)热门网络小说_小说推荐完结下乡被男友造黄谣,我勾上糙汉(周清泽沈云海)
下乡被男友造黄谣,我勾上糙汉(周清泽沈云海)热门网络小说_小说推荐完结下乡被男友造黄谣,我勾上糙汉(周清泽沈云海)
玖日故事
 百万生日宴上张宇周芸免费完结小说_完本完结小说百万生日宴上(张宇周芸)
百万生日宴上张宇周芸免费完结小说_完本完结小说百万生日宴上(张宇周芸)
玖日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