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用父母的寿命换人命一种冰冷免费完结版小说_小说完结用父母的寿命换人命一种冰冷
- 分类: 其它小说
- 作者:思绪随风飞
- 更新:2025-07-16 17:19:03
《用父母的寿命换人命一种冰冷免费完结版小说_小说完结用父母的寿命换人命一种冰冷》精彩片段
过年返乡的最后一班大巴上,我莫名哭到窒息。爸妈无奈带我下车,改签第二天车票。
当晚新闻播报大巴坠崖,全员遇难。父母抱着我喜极而泣:“多亏了我们小宝!
”01鞭炮的残骸在冷风里打着旋儿,红得刺眼,空气里弥漫着散不尽的硝烟味,
混杂着廉价香水和汗气,又闷又浊。候车大厅像个巨大的、喧嚣的罐头,
各种乡音在里面碰撞、挤压。我死死攥着妈妈李秀珍的衣角,布料粗糙,
上面还有洗不掉的油烟味。爸陈建国蹲在对面,下巴绷得紧紧的,像块风干的石头,
手指焦躁地在大背包带子上敲打,眼睛时不时瞟向挂在高处、慢得令人心慌的电子钟。
“最后一班了……挤成啥样也得挤上去!”爸的声音从牙缝里挤出来,
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狠劲儿。他背上那个巨大的、鼓鼓囊囊的蛇皮袋,
像一座沉默的山压在他佝偻的背上。他另一只手又用力提起一个塞得变形的拉杆箱,
箱子轮子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队伍像一条僵死的巨虫,终于开始极其缓慢地向前蠕动。
爸像一头老黄牛,闷着头,用肩膀和胳膊肘在密密匝匝的人墙里硬生生拱开一条缝隙。
妈拉着我,紧贴在他汗湿的后背后面,几乎是被推着向前挪动。各种包裹蹭着我的脸,
劣质皮革和汗味一股脑儿钻进鼻孔,熏得我头晕眼花。终于挤到检票口,
检票员不耐烦地撕了票根,朝身后黑压压的人群吼了一嗓子:“满啦!后面的别挤了!
没票了!”我们几乎是被人流裹挟着冲上了那辆塞得满满当当的大巴。
车厢里浑浊的热浪和更浓烈的汗味、食物味混合着扑面而来,几乎令人窒息。
过道上堆满了行李和人,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爸艰难地把大蛇皮袋塞进行李架的空隙,
又用膝盖顶着,把拉杆箱硬生生塞到座位底下。妈抱着我,几乎是悬空地挤进靠窗的座位,
爸紧挨着我们坐下,立刻被旁边一个胖男人挤得动弹不得。
我的后背紧紧贴着冰冷又布满划痕的车窗玻璃。发动机沉闷地低吼起来,
像一头疲惫不堪的野兽。车身猛地一震,开始缓缓滑出车站。
窗外那些昏黄的路灯和嘈杂的人声被迅速甩开,沉入越来越浓的黑暗里。车厢顶灯熄灭了,
只剩下少数几盏应急灯发出惨淡的绿光,映着一张张疲惫麻木、在颠簸中摇晃的脸。
车轮碾过坑洼路面,整个车身都在痛苦地呻吟、震颤。就在这时,
一种毫无征兆的、冰冷的恐惧感猛地攫住了我。像一只无形的手,瞬间攥紧了我的心脏,
又冷又硬。我猛地抽了一口凉气,那凉气直冲喉咙,带着一种铁锈的腥甜味。
视野里的一切开始疯狂地旋转、扭曲,车窗外的黑暗不再是单纯的夜色,
它仿佛有了粘稠的实体,翻涌着,透出一种不祥的死气。“哇——!!!
”我爆发出的哭声撕破了车厢里沉闷的寂静,尖锐得连自己都害怕。
那不是寻常的耍赖或委屈,是某种源于生命最深处的、纯粹的、对毁灭的恐惧。
眼泪像决堤的洪水,汹涌而出,瞬间糊满了整张脸,滚烫的,带着咸涩的味道流进嘴里。
我拼命踢蹬着双腿,小小的身体在妈妈怀里剧烈地扭动、挣扎,像一条被扔上岸濒死的鱼,
想要不顾一切地逃离这个钢铁的囚笼。“小宝!小宝!咋啦?别哭啊!”妈的声音慌乱不堪,
带着哭腔。她粗糙温暖的手掌用力拍着我的背,又去摸我的额头,
“不烫啊……是不是挤着了?乖啊,马上到家了,马上就能看到奶奶了……”爸也慌了神,
笨拙地伸手过来想抱我,声音又急又躁:“莫哭!男子汉哭啥哭!再哭坏人把你抓走!
”他的威胁在巨大的恐惧面前苍白无力,反而像油浇在火上。我挣扎得更凶了,
小手胡乱挥舞,指甲不知在谁的手背上抓出红痕。我的哭声变成了撕心裂肺的嚎叫,
几乎喘不上气,每一次吸气都带着抽噎和窒息般的倒气声。全车人的目光都聚焦过来,
烦躁的、好奇的、厌恶的……像无数根针扎在皮肤上。有人低声抱怨,有人重重叹气。
“吵死了!管管孩子行不行?”后排传来一个男人不耐烦的吼声。“就是,
还让不让人休息了?明天还要赶路呢!”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附和着。
司机是个满脸横肉的中年汉子,他烦躁地拍了一下方向盘,刺耳的喇叭声猛地炸响:“喂!
后头搞什么名堂!孩子哭成这样管不管了?再闹哄哄的影响开车,都给我下去!
”爸的脸涨成了猪肝色,额角的青筋突突直跳。他看看怀里哭得快要背过气去的我,
又看看周围那些嫌恶的目光,再看看前面司机透过后视镜射来的冰冷眼神。妈紧紧抱着我,
眼泪也无声地往下掉,嘴唇哆嗦着,无助地看着爸。时间仿佛凝固了。
每一秒都被拉得无比漫长,充斥着我的嚎哭和引擎的轰鸣。爸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搐了几下,
那些横肉扭曲着,最后猛地一咬牙,腮帮子绷得死紧。他像是用尽了全身力气,
从牙缝里迸出几个字,声音嘶哑得厉害:“师傅……停车!我们……我们下去!
”车门发出沉重的“嗤”一声,像怪物不情愿地张开嘴。冰冷的夜风猛地灌进来,
带着郊区特有的泥土和荒草的气息,瞬间冲散了车厢里令人窒息的浑浊。
爸几乎是半扛半抱着我,妈踉跄地跟在后面,提着那个巨大的蛇皮袋一角,
狼狈不堪地被“吐”在了路边昏黄的光晕里。大巴车没有丝毫留恋,
巨大的尾灯像两只猩红的眼睛,冷冷地瞥了我们一眼,便轰鸣着加速,
庞大的车身很快被浓墨般的黑暗吞噬,只留下呛人的尾气味在冷风里弥漫。“这下好了!
最后一班车!回不去了!看你闹的!”爸的声音在空旷寂静的夜里炸开,
带着无处发泄的怒火和一种深重的、几乎压垮他的疲惫。
他猛地把我放在冰冷坚硬的水泥地上。寒意立刻穿透薄薄的棉裤,激得我打了个哆嗦,
连带着那几乎撕裂喉咙的嚎哭也骤然止住,只剩下断断续续、控制不住的抽噎。
爸狠狠踹了一脚路边的水泥墩子,发出沉闷的“咚”一声,他背对着我们,
肩膀剧烈地起伏着,像一头受伤的困兽。妈蹲下来,把我紧紧搂在怀里,
用她粗糙的袖子胡乱地擦着我脸上冰凉的泪水和鼻涕。“建国……”她的声音抖得厉害,
带着哭腔,“别怪孩子……小宝是吓着了……肯定是吓着了……”她一遍遍地重复着,
像是在说服爸,更像是在说服自己。不知过了多久,爸才猛地转过身。
路灯昏黄的光打在他脸上,沟壑纵横,写满了无奈和一种认命般的颓丧。“……哭够了?
”他哑着嗓子问,声音低沉,火气似乎被寒风吹散了大半,只剩下深深的无力。他不再看我,
抬头望了望漆黑一片、连颗星星都没有的天。“找个地方窝一宿吧,
明早……看能不能买到票。”附近只有一家破旧得仿佛随时会散架的小旅店,门脸狭窄,
霓虹灯管坏了一半,“宾”字只剩下半个“兵”字在诡异地闪烁。油腻腻的前台后面,
一个头发花白、眼皮耷拉的老头用浑浊的眼睛瞥了我们一眼,丢出一把系着褪色红绳的钥匙,
指了指黑洞洞的楼梯口,便又低下头去看他那台布满雪花点的破旧小电视。房间狭小得可怜,
只有一张吱呀作响的铁架床和一张掉漆的桌子。墙壁斑驳,糊着发黄的旧报纸,
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霉味和劣质消毒水混合的味道。天花板角落,
一张巨大的蛛网在穿堂风里微微颤动。唯一的窗户关不严实,冷风飕飕地往里钻。
妈用热水瓶里一点温吞的水给我擦了脸和手。爸坐在床边唯一那把瘸腿的椅子上,
沉默地卷着旱烟。劣质烟草辛辣刺鼻的气味在狭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
我蜷缩在冰冷的、带着可疑污渍的薄被子里,身体还在不受控制地微微发抖。
那场耗尽所有力气的哭嚎过后,只剩下一种虚脱般的茫然和残余的、沉甸甸的恐惧,
像冰冷的石头压在胸口。窗外是无边无际的黑暗,寂静得可怕。爸偶尔吸一口烟,
烟头的红光在昏暗里明灭,映着他紧锁的眉头。妈疲惫地坐在床边,
把我冰冷的小脚丫捂在她温热的肚子上。她打开那台同样布满雪花点的旧电视,
试图驱散一点这令人窒息的死寂。嘈杂的广告声断断续续地响着。
“……本台最新消息……”主持人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清晰,带着一种职业化的沉重,
瞬间压过了所有的杂音。爸夹着烟卷的手指猛地顿在半空。妈捂着我脚的动作也僵住了,
她下意识地把我搂得更紧,眼睛死死盯住那闪烁的屏幕。“……今日晚间十点十五分左右,
由本市开往青石镇的省道长途客运班车,在途经老鹰嘴盘山公路时,因雨雪路滑,
不幸发生严重坠崖事故……据初步核实,
该班次为今日最后一班……车上司乘人员共四十三人……目前救援工作正在进行中,
步判断……无人生还可能……”屏幕上是晃动的、刺眼的车灯扫过的画面:陡峭漆黑的悬崖,
扭曲断裂的护栏,山崖下隐约可见的、摔得支离破碎的巨大车体残骸,
像一只被踩扁的铁皮罐头,
雪地的映衬下触目惊心……救援人员微弱的手电光在黑暗中徒劳地晃动……房间里死寂一片。
电视屏幕闪烁的光映在爸妈惨白如纸的脸上。爸夹在指间的旱烟无声地滑落,
掉在肮脏的水泥地上,溅起几点火星,瞬间熄灭。他张着嘴,
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无意义的声音,眼睛瞪得滚圆,死死盯着屏幕上那地狱般的景象,
瞳孔里映着跳跃的光点和冰冷的绝望。妈的身体筛糠一样剧烈地抖了起来,
搂着我的手臂勒得我生疼。她猛地低下头,把脸深深埋进我小小的肩窝里。
滚烫的、汹涌的液体瞬间浸透了我的衣服,灼烧着我的皮肤。那不是眼泪,
是劫后余生、混杂着极致恐惧和狂喜的洪流。她的身体抖得那么厉害,
以至于我也跟着剧烈地摇晃起来。“小宝……小宝啊……”她抬起头,脸上涕泪横流,
混杂着一种近乎疯狂的激动和难以置信的狂喜,声音破碎不堪,
“是……是你救了咱家……救了你爸妈的命啊!”她用力地摇晃着我,像是要确认我的存在,
“多亏了你!多亏了我们小宝!菩萨保佑!祖宗显灵啊!”她语无伦次,
粗糙的手指一遍遍抚摸着我的头发、我的脸,仿佛在确认一件失而复得的稀世珍宝。
爸终于从那石化般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他一步跨到床边,
巨大的、带着厚茧和烟草味的手掌猛地伸过来,不是抚摸,
而是近乎粗暴地、重重地拍在我的背上,一下,又一下。
那力道大得让我小小的身体都跟着震动。他什么也没说,
只是喉咙里发出压抑的、如同受伤野兽般的呜咽,眼眶通红,浑浊的泪水终于决堤,
顺着他深刻如刀刻的皱纹汹涌而下,滴落在油腻的床单上,洇开深色的印记。
狂喜的浪潮在狭小的房间里汹涌澎湃,几乎要将屋顶掀翻。爸咧着嘴,那笑容却比哭还难看,
他猛地把我从妈的怀里“夺”过去,用他那粗糙得像砂纸一样的脸使劲蹭着我的脸颊,
胡茬扎得我生疼,烟草味、汗味和一种劫后余生混杂着泪水的咸腥味将我紧紧包裹。
他嘴里反复念叨着:“值了!值了!我儿有灵性!有灵性啊!”声音嘶哑,
带着一种失控的颤抖。妈在一旁又哭又笑,手忙脚乱地从那个巨大的蛇皮袋深处翻找。
她掏出一个用塑料袋裹了好几层的油纸包,小心翼翼地打开,
里面是几块压得有些变形的白糖糕——那是她特意留着路上给我吃的。她掰下一小块,
不由分说地塞进我嘴里,指尖还在微微发颤:“吃!小宝吃!甜的!吃了压压惊!
咱家小宝是福星!是大福星!”白糖糕在嘴里化开,甜得发腻,黏在喉咙里。
爸的拥抱勒得我几乎喘不过气,他身上的味道和那浓烈的情绪像一层厚厚的茧,
将我紧紧束缚。我只觉得胸口发闷,
那沉重的、冰冷的恐惧感并未因这铺天盖地的狂喜而消散半分,反而像水底的淤泥,
被搅动后更加混浊地沉淀在心底。爸妈劫后余生的眼泪是滚烫的,滴在我脸上,
却让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寒意。我僵硬地被爸抱着,眼睛越过他宽厚的肩膀,
茫然地望向窗外那吞噬了一车人的、浓得化不开的黑暗。那黑暗深处,仿佛有什么东西,
正无声地凝视着我们。***日子像村口那条浑浊的小河,看似平静地流淌下去。
大巴车坠崖的惨剧在村里口耳相传,添油加醋,最终变成了一个离奇而悲壮的故事。
而我们一家三口,则成了这个故事里唯一被命运大手捞起的幸运儿。村里人看我们的眼神,
总带着一种奇异的探究和敬畏。“老陈家的娃儿,有灵性哩!”他们私下里都这么说。
爸妈对此深信不疑。那份失而复得的狂喜,沉淀成了对我近乎偏执的珍视和小心翼翼的呵护。
爸在砖窑厂干活时,腰板似乎挺得更直了些,沉默寡言依旧,
但眉宇间那常年盘踞的愁苦淡去了不少。妈在田里忙活,
回家时总会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摸出点野果、烤红薯之类的小东西塞给我,
粗糙的手摸摸我的头,笑容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满足和庆幸。只有我自己知道,那晚之后,
有些东西不一样了。一种冰冷的东西,像蛇一样钻进了我的骨头缝里,盘踞不去。
最初的变化是无声无息的。那天,隔壁王奶奶拄着拐棍,
慢悠悠地挪到她家院门口的石墩子上晒太阳。冬日的阳光很薄,没什么暖意。
我正蹲在自家门槛上玩几块捡来的彩色玻璃片。阳光透过玻璃片,
在地上投下小小的、扭曲的光斑。我无意间抬起头,看向王奶奶。就在那一瞬间,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猛地一抽。王奶奶头上,那稀疏花白的发丝之间,
赫然悬浮着一圈……数字!是血一样的、粘稠的红色。它们无声地跳动着,
00:03:17……00:03:16……00:03:15……那红色刺得我眼睛生疼,
一股冰冷的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我惊得猛地向后一仰,
手里的彩色玻璃片“哗啦”一声全掉在地上,摔得粉碎。“小宝?咋啦?
”妈闻声从灶房里探出头,手上还沾着湿漉漉的菜叶子。我张着嘴,喉咙像是被堵住了,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死死盯着王奶奶头上的数字,
:00:01:05……00:01:04……“王……王奶奶……”我艰难地挤出几个字,
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手指不受控制地指向她。就在这时,
王奶奶大概是坐久了想站起来活动活动。她一手扶着拐棍,一手撑向旁边的石墩子,
身子刚微微抬起一点,那只支撑的手却猛地一滑!拐棍脱手飞了出去,
她枯瘦的身体像一截失去支撑的朽木,直挺挺地、重重地向后仰倒!“砰!
”沉闷的撞击声在寂静的午后格外惊心。
她的后脑勺结结实实地磕在了身后冰冷坚硬的青石门槛上。
的红色数字在撞击发生的刹那——00:00:00——像肥皂泡一样无声地破裂、消散了。
“哎哟!我的老天爷!”妈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冲了过去。王奶奶躺在地上,
身体微微抽搐着,眼睛瞪得老大,浑浊的眼珠里映着灰蒙蒙的天空,
口鼻间迅速涌出暗红的血沫。她喉咙里发出“嗬嗬”的、拉风箱似的声音,
身体最后剧烈地弹动了一下,便彻底瘫软不动了。妈扑在她身上,慌乱地哭喊着。
邻居们闻声围拢过来,七手八脚,一片混乱。我僵在原地,像一尊石雕。手脚冰凉,
牙齿不受控制地磕碰着,发出“咯咯”的轻响。刚才那血红的倒计时,
王奶奶倒地时那沉闷的声响,还有她头上数字归零时瞬间的碎裂感……像冰冷的烙铁,
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王奶奶是村里的孤寡老人,她的葬礼很简单。下葬那天,
天空飘着细密冰冷的雨丝。爸沉默地跟着去帮忙抬棺。妈回来时,眼圈红红的,
坐在灶膛前的小板凳上发呆。跳跃的火光映着她疲惫的脸。“唉,人老了,
不中用……”妈长长地叹了口气,声音沙哑,“王婶子苦了一辈子,走的时候……太遭罪了。
”她抬起手,习惯性地想揉揉眼睛,动作却突然顿住了。她的手指停在自己右边的眼角下方,
那里,在跳跃的火光映照下,一道细细的、之前从未留意过的皱纹,
似乎比旁边的痕迹要深那么一点点,像一条极淡的刻痕。我的心,像被那冰冷的雨丝浸透,
一点点沉下去。***王奶奶的死在村里引起了一阵短暂的唏嘘,很快又被日常的琐碎淹没。
只有我,像个怀揣着巨大秘密的幽灵,在看似平静的日子里,
被那冰冷而诡异的“天赋”反复折磨。不久后,村西头的李二狗,
一个整天乐呵呵、喜欢在村口大槐树下吹牛的壮实汉子,
成了我视野里第二个顶着“倒计时”的人。那天傍晚,夕阳像熔化的金子,泼洒在村道上。
李二狗刚帮人杀完猪,脸上还溅着几点没擦干净的血星子,扛着半扇猪肉,哼着小调往家走。
着:00:05:49……00:05:48……那鲜红的颜色和他脸上的血点混合在一起,
显得格外狰狞。恐惧像藤蔓一样缠绕住我的心脏,越收越紧。我认得他,
他总爱用他那蒲扇般的大手揉乱我的头发,塞给我一把炒豆子。
我看着他头上的数字一秒一秒地无情跳减,巨大的恐慌攫住了我。不行!不能像王奶奶那样!
我脑子里只剩下这一个念头。“二狗叔!二狗叔!”我像颗小炮弹一样猛地从家门口冲出去,
带着哭腔,用尽全身力气扑向他。李二狗被我撞得一个趔趄,差点没站稳,
肩上那半扇沉甸甸的猪肉也晃悠了一下。“哎哟!小宝?你这娃儿,咋啦?慌慌张张的!
同类推荐
 丈夫的女秘书罚我做保洁后,工厂完了朱明明郑合免费小说在线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丈夫的女秘书罚我做保洁后,工厂完了(朱明明郑合)
丈夫的女秘书罚我做保洁后,工厂完了朱明明郑合免费小说在线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丈夫的女秘书罚我做保洁后,工厂完了(朱明明郑合)
玖日故事
 亲爹祭天,她沉重的爱我不要了陆涛苏青好看的小说推荐完结_在哪看免费小说亲爹祭天,她沉重的爱我不要了陆涛苏青
亲爹祭天,她沉重的爱我不要了陆涛苏青好看的小说推荐完结_在哪看免费小说亲爹祭天,她沉重的爱我不要了陆涛苏青
玖日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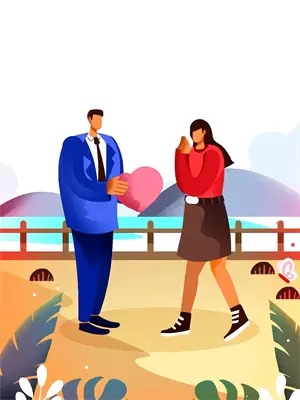 婆婆选我死后发现我才是亲生的(周润言林秀玉)免费完结小说_免费小说在线阅读婆婆选我死后发现我才是亲生的(周润言林秀玉)
婆婆选我死后发现我才是亲生的(周润言林秀玉)免费完结小说_免费小说在线阅读婆婆选我死后发现我才是亲生的(周润言林秀玉)
玖日故事
 儿子毕业旅行被困沙漠沈心柔陆景山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儿子毕业旅行被困沙漠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儿子毕业旅行被困沙漠沈心柔陆景山最新章节免费阅读_儿子毕业旅行被困沙漠全文免费在线阅读
玖日故事
 用黑卡请舍友吃饭,我倒欠一个亿(柳萌萌朱炎)热门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用黑卡请舍友吃饭,我倒欠一个亿(柳萌萌朱炎)
用黑卡请舍友吃饭,我倒欠一个亿(柳萌萌朱炎)热门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用黑卡请舍友吃饭,我倒欠一个亿(柳萌萌朱炎)
玖日故事
 我把信用卡刷爆后,想整容的表姐疯了江川乔念安热门的小说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我把信用卡刷爆后,想整容的表姐疯了江川乔念安
我把信用卡刷爆后,想整容的表姐疯了江川乔念安热门的小说_热门小说在线阅读我把信用卡刷爆后,想整容的表姐疯了江川乔念安
玖日故事
 重生后我为三皇子驭灵成兵(驭灵顾逸川)网络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重生后我为三皇子驭灵成兵(驭灵顾逸川)
重生后我为三皇子驭灵成兵(驭灵顾逸川)网络热门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重生后我为三皇子驭灵成兵(驭灵顾逸川)
玖日故事
 身为貔貅的我不再替老公转运宋晩绮谢归舟完整免费小说_热门小说阅读身为貔貅的我不再替老公转运宋晩绮谢归舟
身为貔貅的我不再替老公转运宋晩绮谢归舟完整免费小说_热门小说阅读身为貔貅的我不再替老公转运宋晩绮谢归舟
玖日故事
 下乡被男友造黄谣,我勾上糙汉(周清泽沈云海)热门网络小说_小说推荐完结下乡被男友造黄谣,我勾上糙汉(周清泽沈云海)
下乡被男友造黄谣,我勾上糙汉(周清泽沈云海)热门网络小说_小说推荐完结下乡被男友造黄谣,我勾上糙汉(周清泽沈云海)
玖日故事
 百万生日宴上张宇周芸免费完结小说_完本完结小说百万生日宴上(张宇周芸)
百万生日宴上张宇周芸免费完结小说_完本完结小说百万生日宴上(张宇周芸)
玖日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