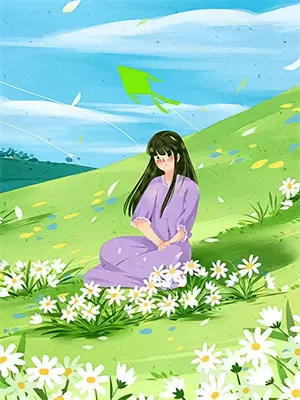- 竹影深·断袖缘
- 分类: 言情小说
- 作者:临梦泽
- 更新:2025-09-23 19:51:10
《竹影深·断袖缘》精彩片段
第一章 雨轩初遇暮春的雨,是临安城最软的缠绵。雨丝细如蚕娘吐出的银丝,织着雾,
缠着风,把满城青石板润得发亮,连街角老槐树的根须都似在雨里舒展了几分。
沈砚之撑着柄杭绸油纸伞,伞面是他亲手选的素色,又请绣娘用墨线绣了几竿疏竹,
竹叶沾雨,仿佛下一秒就要从伞面滴落。他新授翰林院编修不过半月,
官袍的青蓝色还带着浆洗后的挺括,今日是应好友画圣苏清寒之邀,
往城西的“听竹轩”赏雨观竹。转过巷口,便见听竹轩的黛瓦翘角隐在雨雾里,
檐下挂着的铜铃被风拂得轻响,混着雨打竹叶的沙沙声,倒比京中戏楼的昆曲还悦耳。
沈砚之收了伞骨,指尖刚触到雕花木门的铜环,一阵风便裹着雨丝扑进来,
沾湿了他衣袍的一角,凉意顺着布料漫到腰间。他抬眼时,
先撞进眼底的不是苏清寒熟悉的身影,而是窗边临帖的少年。少年穿件月白长衫,
料子是江南常见的细棉布,领口袖口都浆洗得干干净净,墨发用根羊脂玉簪松松束在脑后,
几缕碎发垂在颊边,被雨气濡湿,贴在细腻的皮肤上。他指尖捏着支狼毫,
正俯身蘸了朱砂在宣纸上落笔,腕骨纤细,却稳得很。雨光透过窗棂落在他侧脸,
勾勒出柔和的下颌线,连垂着眼睫时投在纸上的阴影,
都像苏清寒画里最精心的工笔——淡墨勾边,浅彩晕染,多一分则艳,少一分则寡。
“砚之倒是准时。”苏清寒从内室掀了竹帘走出,手里还捏着支兼毫笔,
指尖沾着些石青颜料,半幅未完成的《竹石图》摊在案上,竹节苍劲,石纹斑驳,
只缺几笔竹叶便算完工。他笑着朝少年抬了抬下巴,“给你介绍,这是我远房表弟谢临舟,
上月刚从江南苏州来,暂住在我这儿。这孩子性子静,平日里就爱躲在轩里写写画画。
”谢临舟这时才停下笔,握着狼毫的手轻轻一顿,朱砂在纸上点出个极小的红点。
他转过身来,比沈砚之矮了小半头,抬头时目光撞进沈砚之眼底,像受惊的小鹿般晃了晃,
随即连忙放下笔,躬身行礼,袍角扫过地面,带起一缕淡淡的墨香:“见过沈大人。
”声音清润,像雨后竹叶上滚落的水珠,砸在青石板上,脆生生的,
还带着点江南水乡的软意。沈砚之收回目光,抬手拱手回礼,
指尖的凉意还没散去:“不必多礼,私下里叫我沈砚之便好。”他迈步走到桌边,
目光落在宣纸上——是王献之的《洛神赋十三行》,字迹清隽秀雅,笔锋间带着江南的温润,
却在“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那句旁,用朱砂点了个极小的墨点,像是犹豫了许久,
终究没敢落下那笔转折。“字是好字,筋骨都在,就是少了点锋芒。
”沈砚之指尖悬在纸上方,没敢碰到未干的墨迹,目光掠过少年写得工整的笔画,
“江南水土养人,也养出这样温润的笔意,可若想写出洛神的‘惊鸿’气,
还得在起笔收锋时,多添几分硬气。”谢临舟闻言,眼睛倏地亮了,像雨雾里透出的光,
他往前凑了半步,袖口带着的墨香混着雨气飘到沈砚之鼻尖,
清清爽爽的:“沈大人也懂书法?我总觉得这字写出来软趴趴的,像没睡醒的猫儿,
听您一说,倒像是拨开了眼前的雾。”他说着,指尖轻轻蹭了蹭宣纸,语气里带着几分期待,
“您……您能教教我吗?”苏清寒在一旁端了杯雨前龙井递过来,
笑着打趣:“你倒会抓机会,砚之的书法,在京城文人圈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去年宫宴上,
皇上还夸过他写的楷书呢。”沈砚之接过茶盏,指尖触到温热的瓷壁,
再看向谢临舟那双满是期待的眼睛,喉结轻轻动了动,终究点了头:“也好,往后若得空,
便来轩中一同练字。”第二章 竹窗伴砚自那日约定后,沈砚之去听竹轩的脚步,
比去翰林院当值还勤。有时是午后,雨停了,阳光透过竹窗筛下碎金般的光,
落在铺好的宣纸上,像撒了把细闪的金粉。沈砚之会先磨墨,墨块是徽州产的老松烟墨,
在砚台里顺时针打转,磨出的墨汁浓淡适宜,带着淡淡的松木香。谢临舟就坐在一旁看,
手里攥着支洗净的狼毫,眼神跟着沈砚之的动作转,像只专注的小雀。等墨磨好,
沈砚之便站到谢临舟身后,左手轻轻扶着少年的手腕,右手覆在他手背上,带着他起笔。
“写‘横’要如千里阵云,起笔藏锋,行笔稳,收笔回锋。”他的声音贴着谢临舟的耳际,
温热的气息扫过少年的耳廓,惹得谢临舟耳尖泛红,握笔的手微微发颤。
沈砚之能清晰感受到少年掌心的温度,还有因紧张而绷紧的指节——像初春刚抽芽的竹枝,
软却韧。他放缓了动作,一点点带着谢临舟运笔,笔尖在宣纸上划过,留下一道平稳的横画。
“对,就是这样,别慌。”他轻声鼓励,指尖偶尔碰到谢临舟的手背,
两人都像被烫到般顿一下,却没人先松开手。有时是傍晚,晚霞把半边天染成胭脂色,
连听竹轩外的竹林都被镀上了层暖红。两人会搬两张竹椅坐在檐下,谢临舟抱着个青瓷茶罐,
给沈砚之续茶,絮絮叨叨讲江南的趣事。“我家后院有棵老竹,比我爹的年纪还大。
”谢临舟捧着茶盏,眼神里满是怀念,“每年春天都会冒新笋,我小时候总爱蹲在旁边看,
盼着笋子快点长高,好让我爹给我做毛笔杆。有次等不及,还偷偷拔了棵刚冒头的笋,
结果被我爹罚抄了三遍《千字文》。”沈砚之听得笑出声,
指尖轻轻敲了敲茶盏:“那后来呢?笋子做成笔杆了吗?”“哪能啊。”谢临舟也笑,
眼尾弯成个好看的弧度,“那笋子太小,根本做不了笔杆,最后被我娘切碎了,
炖了竹荪笋干汤,鲜得很。”他顿了顿,又补充道,“等咱们以后去江南,
我带你去看那棵老竹,现在它的枝干,都够做十几支好笔了。”“好。”沈砚之应得干脆,
目光落在谢临舟带着笑意的脸上,心里像被温水浸过,软得一塌糊涂。他从没去过江南,
却从谢临舟的话里,拼出了一个满是水汽与花香的江南——有西湖的桃花雨,
有巷口的桂花糖粥,还有一棵等着他们去看的老竹。日子久了,
听竹轩里渐渐多了些细碎的暖意。沈砚之会记得谢临舟爱喝的雨前龙井,
每次来都带一小罐;谢临舟会提前把沈砚之常用的那支兼毫笔洗净晾好,连砚台都擦得锃亮。
有时沈砚之在翰林院被差事绊住,来得晚了,推开门总能看见谢临舟坐在窗边,手里捏着笔,
却没写字,只是望着窗外的竹林发呆,见他来,眼睛会瞬间亮起来,像星星落进了眼底。
苏清寒看在眼里,偶尔会打趣两句:“你们俩现在,倒比我这主人还亲。
”沈砚之会耳根泛红,谢临舟则低下头,指尖轻轻蹭着袖口,却没人反驳。
这份藏在竹影与墨香里的情意,像檐下的藤蔓,悄无声息地生长,缠上了彼此的心头。
第三章 乞巧诉心七月初七乞巧节,京城的街上满是热闹。姑娘们提着绣着鸳鸯的花灯,
小伙子们捧着刚买的胭脂水粉,连空气里都飘着甜意。沈砚之从集市上挑了盏走马灯,
灯面是上好的桑皮纸,画着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图样,灯芯是浸了蜡的棉线,一点燃,
暖黄的光透过纸面,把牛郎织女的影子投在地上,一转动,便似在灯里走动。
他提着灯往听竹轩去,心里揣着点说不清的紧张,像揣了只乱撞的兔子。推开门时,
却没见往常等在窗边的谢临舟。沈砚之往里走了两步,才看见谢临舟站在案前,
对着一幅画发呆。画是苏清寒刚完成的《寒江独钓图》,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意境清冷,可谢临舟的目光,却死死落在画旁的一行小字上——“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已老”。“在看什么?”沈砚之把走马灯放在桌上,点燃灯芯,暖黄的光漫开来,
柔和了谢临舟眉间的愁绪。谢临舟猛地回神,眼底的湿意还没散去,慌忙用袖口擦了擦,
却没擦干净,留下淡淡的水痕。“没什么,就是觉得这字写得……可怜。”他顿了顿,
声音低了些,像被雨打湿的棉线,软得发沉,“沈大人,您说……人这一辈子,
是不是总有求而不得的事?比如想留的人留不住,想做的事做不成。
”沈砚之看着他泛红的眼角,心像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疼得发紧。他往前走了一步,
离谢临舟只有半步远,能看清他眼睫上还挂着的小泪珠,像清晨竹叶上的露珠。“临舟,
你想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都给你。”谢临舟抬眼看他,目光里带着几分慌乱,几分试探,
还有几分藏了许久的情意——像埋在土里的竹芽,终于要破土而出。
“我想要……能一直和你一起练字,一起看竹,一起说江南的事。”他的声音发颤,
指尖攥紧了衣摆,“可我知道,您是朝廷命官,将来要娶名门闺秀,要生儿育女,
最新章节
同类推荐
猜你喜欢
 张伟李曼(全公司都等我滚,我等我爸退休)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张伟李曼全集在线阅读
张伟李曼(全公司都等我滚,我等我爸退休)全本免费在线阅读_张伟李曼全集在线阅读
芋儿仙草冻
 结婚三年不孕,丈夫竟和白月光生子逼我让位(秦墨陆哲)新热门小说_免费完结小说结婚三年不孕,丈夫竟和白月光生子逼我让位(秦墨陆哲)
结婚三年不孕,丈夫竟和白月光生子逼我让位(秦墨陆哲)新热门小说_免费完结小说结婚三年不孕,丈夫竟和白月光生子逼我让位(秦墨陆哲)
财源广进财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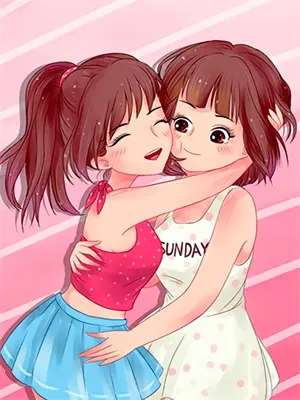 结婚三年,老公竟和白月光有个三岁娃(江川白月光)最新完结小说推荐_热门小说排行榜结婚三年,老公竟和白月光有个三岁娃江川白月光
结婚三年,老公竟和白月光有个三岁娃(江川白月光)最新完结小说推荐_热门小说排行榜结婚三年,老公竟和白月光有个三岁娃江川白月光
软绵无力的尤尼萨
 焰草相依唐烨唐三热门小说排行_免费小说焰草相依唐烨唐三
焰草相依唐烨唐三热门小说排行_免费小说焰草相依唐烨唐三
风止枕月
 媚药焚心后,我成了帝王心尖人(温如昔萧彻)在线阅读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媚药焚心后,我成了帝王心尖人(温如昔萧彻)
媚药焚心后,我成了帝王心尖人(温如昔萧彻)在线阅读免费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媚药焚心后,我成了帝王心尖人(温如昔萧彻)
酒徒老九
 《他以温柔入局》姜轻烟顾盛已完结小说_他以温柔入局(姜轻烟顾盛)经典小说
《他以温柔入局》姜轻烟顾盛已完结小说_他以温柔入局(姜轻烟顾盛)经典小说
木棉suki
 被出轨男友骗光钱财骗到缅甸,死无全尸(柳如烟李林)最新完结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被出轨男友骗光钱财骗到缅甸,死无全尸(柳如烟李林)
被出轨男友骗光钱财骗到缅甸,死无全尸(柳如烟李林)最新完结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被出轨男友骗光钱财骗到缅甸,死无全尸(柳如烟李林)
作者e1k7ou
 重回九零我悔婚当天嫁给了冷面军官(苏雅雅江北辰)最新完结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重回九零我悔婚当天嫁给了冷面军官(苏雅雅江北辰)
重回九零我悔婚当天嫁给了冷面军官(苏雅雅江北辰)最新完结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重回九零我悔婚当天嫁给了冷面军官(苏雅雅江北辰)
锦字流年
 重生后她们都想养成我?我成资本大佬了(苏晴林默)免费小说笔趣阁_完结版小说推荐重生后她们都想养成我?我成资本大佬了(苏晴林默)
重生后她们都想养成我?我成资本大佬了(苏晴林默)免费小说笔趣阁_完结版小说推荐重生后她们都想养成我?我成资本大佬了(苏晴林默)
努力生活农家子
 重生九零嫁给军官后我成了团宠(晓雯沈北辰)热门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重生九零嫁给军官后我成了团宠(晓雯沈北辰)
重生九零嫁给军官后我成了团宠(晓雯沈北辰)热门小说_完结版小说全文免费阅读重生九零嫁给军官后我成了团宠(晓雯沈北辰)
八方来财来财财财
 金笼雀债我掀了霸总的天许雾傅凛小说完整版免费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金笼雀债我掀了霸总的天(许雾傅凛)
金笼雀债我掀了霸总的天许雾傅凛小说完整版免费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金笼雀债我掀了霸总的天(许雾傅凛)
觅芊重生
 瑶光劫苏瑶的复仇之旅沈逸风苏瑶完整版在线阅读_沈逸风苏瑶完整版阅读
瑶光劫苏瑶的复仇之旅沈逸风苏瑶完整版在线阅读_沈逸风苏瑶完整版阅读
天使不听话
 萧玦苏绾嫡女归来王爷,别来无恙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萧玦苏绾完整版阅读
萧玦苏绾嫡女归来王爷,别来无恙最新章节在线阅读_萧玦苏绾完整版阅读
书狂散人
 摊牌倒计时当我管家开直升机来接我,前妻全家傻眼了(张伟林玥)无弹窗小说免费阅读_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摊牌倒计时当我管家开直升机来接我,前妻全家傻眼了张伟林玥
摊牌倒计时当我管家开直升机来接我,前妻全家傻眼了(张伟林玥)无弹窗小说免费阅读_小说免费阅读无弹窗摊牌倒计时当我管家开直升机来接我,前妻全家傻眼了张伟林玥
紫茶柚
 他撞了我三年不来看,却天天陪着冒充我的女人(许向南顾寒川)完结版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他撞了我三年不来看,却天天陪着冒充我的女人许向南顾寒川
他撞了我三年不来看,却天天陪着冒充我的女人(许向南顾寒川)完结版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他撞了我三年不来看,却天天陪着冒充我的女人许向南顾寒川
喜欢稗草的荣荣
 云城浮世绘断线风筝与琥珀时光顾城苏瑶完整版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云城浮世绘断线风筝与琥珀时光(顾城苏瑶)
云城浮世绘断线风筝与琥珀时光顾城苏瑶完整版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云城浮世绘断线风筝与琥珀时光(顾城苏瑶)
24468667
 结婚五年,老公和白月光的三岁儿子叫我妈林晚晚陆珩热门小说阅读_完本完结小说结婚五年,老公和白月光的三岁儿子叫我妈林晚晚陆珩
结婚五年,老公和白月光的三岁儿子叫我妈林晚晚陆珩热门小说阅读_完本完结小说结婚五年,老公和白月光的三岁儿子叫我妈林晚晚陆珩
不赚一个亿不收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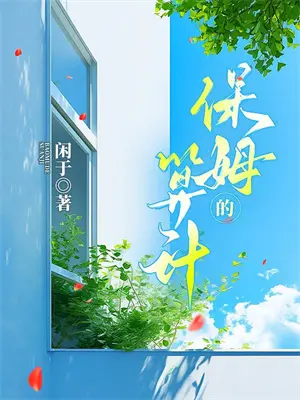 你不爱我,可我死了你哭什么江晴厉飞潇免费小说全文阅读_免费小说在线阅读你不爱我,可我死了你哭什么江晴厉飞潇
你不爱我,可我死了你哭什么江晴厉飞潇免费小说全文阅读_免费小说在线阅读你不爱我,可我死了你哭什么江晴厉飞潇
偷一只小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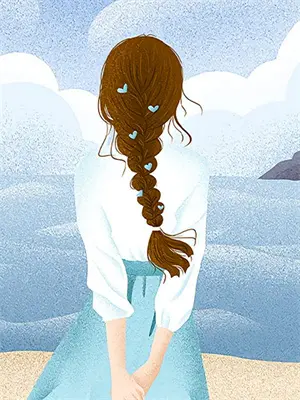 《我死后15年,老公娶了白月光还杀我全家》陈卓顾呈言完本小说_陈卓顾呈言(我死后15年,老公娶了白月光还杀我全家)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我死后15年,老公娶了白月光还杀我全家》陈卓顾呈言完本小说_陈卓顾呈言(我死后15年,老公娶了白月光还杀我全家)全文免费阅读无弹窗大结局
青灯古卷度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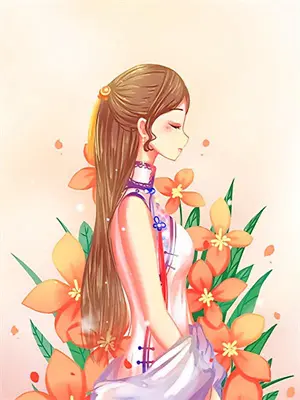 做美食主播月入十万,却发现帮助我的人另有目的(苏语嫣陆景深)热门网络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做美食主播月入十万,却发现帮助我的人另有目的(苏语嫣陆景深)
做美食主播月入十万,却发现帮助我的人另有目的(苏语嫣陆景深)热门网络小说_最新章节列表做美食主播月入十万,却发现帮助我的人另有目的(苏语嫣陆景深)
喜欢稗草的荣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