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四季物语小寒·酥醒
- 分类: 都市小说
- 作者:云烟极光
- 更新:2025-09-19 18:15:25
《四季物语小寒·酥醒》精彩片段
第一章 寒酥小寒时节的江南水乡,是一年中最彻骨清寒的光景。河水凝滞如墨,
倒映着铅灰色的天空,岸边枯苇挂满晶莹的霜棱,在稀薄的阳光下闪烁如碎钻。空气干冷,
呼吸间带着刺肺的凉意,风吹过老街巷的黛瓦白墙,发出萧瑟的呜咽。万物蛰伏,
天地间一片沉寂,唯有那无处不在的寒意,如同无声的潮水,浸透每一寸砖石与肌骨。
在这片冰封般的静谧中,一种温暖而诱人的气息,
、上等猪油融化后的醇厚乳香、慢火细熬的红豆沙的甜润、以及若有若无的糖蜜和桂花气息。
这香气穿透清冷的空气,如同一条无形的暖线,牵引着偶尔路过的行人。香气的源头,
是一家名为“沁芳斋”的老式茶食铺。门面狭小,木格窗棂,一块乌木旧匾额悬于门上,
字迹已被岁月磨蚀得有些模糊。推门而入,铜铃轻响,暖意混着更浓郁的甜香扑面而来。
店内光线偏暗,却异常洁净。
着几样简单的糕点:酥皮微黄的白麻饼、色泽深褐的百果蜜糕、雪白中透出豆沙馅的定胜糕,
样式古朴,并无太多花哨。柜台后,
一位头发花白、精神却显矍铄的老者苏老先生正戴着老花镜,
用一把小铲刀小心地给刚出炉的松子枣泥酥点上红印。他的动作舒缓而专注,
带着一种经年累月形成的韵律感。店铺后半部分与后厨相连,帘子半掀,
可见一个穿着素色棉麻围裙的年轻女子正俯身在一个宽大的案板前。
她手中握着一根长长的枣木擀面杖,正用力碾压着一团油润的面团,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
她是老先生的孙女,苏予甜。案板上,
还散落着一些雕花模具、小铜秤、以及盛着各色馅料的青花瓷碗。“爷爷,
这批‘玉露霜’的粉,我按您说的,又多炒了一刻钟,您闻闻这火候对不对?
”苏予甜抬起手臂擦了擦额角,扬声问道,声音清润。苏老先生放下铲刀,深吸一口气,
眯眼品了品:“嗯,成了。炒粉要的就是这个‘焦香入骨却不苦’的劲儿,差一分则生,
过一分则糊。下次记得,灶火要比今天再弱半分。”就在这时,店门上的铜铃又响了。
一个身影推门而入,带进一股冷风。来人是个三十出头的男子,穿着半旧的深色羽绒服,
围巾遮住了下半张脸,肩上落着赶路带来的寒尘。他身形清瘦,
背着一个看起来颇有些分量的双肩包,眼神沉静,却带着一种长途跋涉的疲惫与风霜。
他的目光第一时间没有看向人,而是快速扫过柜台里的糕点,鼻翼微不可察地动了动,
像是在仔细分辨空气中的每一种气味成分。最后,
他的目光落在苏予甜手下那团正在被反复折叠碾压的面团上,眼神微凝。
“请问…还有‘雪窗寒帖’吗?”男子开口,声音低沉,略带沙哑,语气直接。
苏予甜抬起头,有些讶然。苏老先生也转过身,推了推老花镜,打量着他。“雪窗寒帖?
”苏予甜摇摇头,“客人,您记错了吧?我们店里没有这款点心。”男子沉默了一下,
从背包侧袋掏出一本翻得卷边的旧笔记本,打开一页,递过来。
纸上用钢笔细致地画着一种造型如微型墨锭、表面有细密酥纹的点心草图,
旁边标注着“酥皮、芝麻馅、微甜、有墨香?”等字样,
下方一行小字:“据《中馈录》推演,或存于沁芳斋?”“《中馈录》?
”苏老先生眼中闪过一丝惊异,“那是本老食谱了,你怎么…”“晚辈顾时安。
”男子取下围巾,露出一张清瘦却轮廓清晰的脸,
眉眼间带着一种长期专注于细微之物的沉静与疏离,“从事传统食品研究。
根据一些线索推断,‘雪窗寒帖’可能与贵店有渊源,特来求证。”他的话语专业而冷静,
并无太多寒暄之意。苏予甜好奇地打量着他。顾时安…这个名字和他的人一样,
带着一种安静而执着的书卷气。“店里确实没有这款点心。”苏老先生沉吟道,“不过,
‘雪窗寒帖’这名字…我好像听我父亲提起过,说是祖上一位喜欢附庸风雅的先人,
照着古书瞎琢磨出来的玩意儿,工艺极繁复,早就失传了。你怎么会找到这里?
”顾时安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失望,
但很快恢复平静:“一些零散的旧笔记和地域物产志提到,贵店早年以几款文人茶点闻名,
‘雪窗寒帖’或是其中之一。晚辈想尝试复原这款古点,所以冒昧前来,
想看看能否找到一点配方或工艺的线索。”苏予甜闻言,眼睛微微一亮。
她对店里这些老配方向来极有兴趣。苏老先生却摆摆手:“年头太久,早就没影儿的事了。
现在店里就靠这几样老基础点心撑着,花样翻新?谈何容易。”语气中带着几分现实的无奈。
正说着,店外传来一阵与这老铺氛围格格不入的爽朗笑声。
一个穿着时髦羊绒大衣、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中年男子,领着一位助理模样的年轻人,
推门而入。“苏老爷子!予甜姑娘!忙着呢?”男子声音洪亮,笑容热络却难掩精明,“哟,
有客人?也是来买点心的?”他瞥了顾时安一眼,见其衣着普通,并未太在意。“金经理。
”苏予甜的语气淡了些,显然认识来人。“哎,别这么生分嘛!
”金经理自顾自地拿起柜台里一块枣泥酥看了看,“还是老几样啊?老爷子,予甜姑娘,
上回我跟您二位提的那个合作方案,考虑得怎么样啦?
我们‘酥礼坊’绝对是带着最大诚意来的!”他语速飞快:“‘沁芳斋’这老牌子,
多有底蕴!就是太…太朴实了!跟我们合作,品牌、资金、设计、营销,我们全包!
把配方优化一下,生产线一上,包装设计得国潮一点,往各大商超、网红渠道一铺!
保证比您现在守着这小炉子,赚得多得多!”苏老先生脸色沉了下来:“金经理,
点心不是这么做的。我们的酥皮,靠的是手工一遍遍擦酥起层;豆沙馅,
得用陈年铁锅慢火翻炒三小时以上。机器流水线,温度时间卡得再准,也出不来这个味儿。
”“老爷子,您得与时俱进啊!”金经理不以为然,
“现在年轻人谁有功夫品您这‘慢工细活’?要的是快、是好看、是话题!您出技术和牌子,
我们负责让它‘潮’起来,利润分成好商量!”苏予甜忍不住开口:“金经理,
沁芳斋的点心,吃的就是手艺和时间的味道。变成工业化产品,就算还叫这个名字,
也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哎哟,我的予甜姑娘!”金经理夸张地叹口气,
“情怀不能当饭吃啊!您看看这街面,游客要的是打卡拍照,
谁真在乎您这点心是揉了八十一遍还是炒了三小时?咱们得迎合市场!
”一直沉默旁观的顾时安忽然开口,声音平静无波:“金经理,
食品工业追求的是标准化和效率,传统手工追求的是风味的独特性和工艺的人文价值。
两者本无高下,但若为了规模化而牺牲风味内核和工艺精髓,甚至模糊其间的界限,
是对传统的消费,而非传承。”他的话,像一杯冷水,浇得金经理的热情稍微降温。
苏予甜则有些惊讶地看了顾时安一眼。金经理干笑两声:“专家就是专家,说话在理!
所以我们才更需要和苏老这样的权威合作,把经验转化为科学嘛!”最终,他留下名片,
强调“机会难得”,悻悻而去。店内重归安静,却因这场闹剧,气氛略显凝滞。
顾时安沉默片刻,对苏老先生道:“老先生,即便没有‘雪窗寒帖’的线索,
不知晚辈能否…购买几款贵店的招牌点心?想仔细品尝学习。”苏老先生脸色稍霁,
点了点头。予甜手脚麻利地装好几样点心,用油纸包好,细绳扎起。顾时安付了钱,
接过点心,微微颔首:“多谢。打扰了。”临走前,
他目光再次扫过苏予甜案板上那团光泽油润的面团,忽然道:“擦酥时,猪油和温水的比例,
若能根据当日气温湿度微调半厘,层酥效果或可更佳。”苏予甜一怔。
这是极细微的经验之谈,非深谙此道者不能察觉。“…受教了。”她轻声道。
顾时安推门而出,融入门外灰白的天光里。苏予甜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巷口,
低头看了看手中那张画着“雪窗寒帖”的纸片,心中泛起一丝奇异的感觉。
苏老先生叹了口气:“又一个钻故纸堆的…如今这世道,静下心来做好眼前这几样,
已是不易了。”窗外,天色愈发阴沉,寒风卷着零星的雪籽,敲打在玻璃窗上。真正的初雪,
似乎快要来了。沁芳斋内,甜香依旧,却仿佛被注入了一丝不同寻常的变数。
一个追寻古味的食研者,一家坚守老味的小铺,以及一场迫在眉睫的商业浪潮。
小寒的冷意中,一场关于味道、传承与未来的故事,正悄然拉开序幕。
第一章 完第二章 糖霜金经理那番“工业化”、“市场化”的论调,
如同小寒时节一阵裹挟着商业冰碴的冷风,刮过沁芳斋后,留下的是更深的凝滞与寒意。
他那套追求效率与流量的逻辑,与店内专注手工、讲究时令与火候的氛围格格不入,
却像一根尖锐的冰棱,刺破了苏老先生和苏予甜一直试图守护的宁静,
让他们更清晰地看到传统手艺在当代的脆弱与窘迫。
顾时安那番关于“风味内核”与“工艺精髓”的冷静辨析,虽暂时噎住了金经理,
在小小茶食铺上空的阴云——现实的经营压力、配方的失传、以及外部虎视眈眈的商业吞噬。
然而,顾时安这个意外的闯入者,也像一粒投入温水的酥糖,虽未立刻融化,
却悄然带来一丝不同寻常的甜意与变化。他并未因“雪窗寒帖”线索中断而立刻离开,
反而真的在古镇一家老客栈住了下来,每日都会来沁芳斋,买上几样不同的点心,
然后坐在临窗的小桌旁,极其专注地品尝。他的品尝方式,与普通食客截然不同。
他会将一块点心仔细分成几份,观察切面的气孔层次、馅料色泽;用小叉子取一小块,
放入口中,并不立刻咀嚼,而是让其在舌尖慢慢融化,
感受油脂的润度、甜度的渗透、香气的层次;有时甚至会拿出一个小笔记本,
快速记录下几笔,眉头微蹙,似在分析思考。这种近乎学术研究般的吃法,
引起了苏予甜极大的好奇。“顾先生,是我们的点心…有什么问题吗?”一次,
她终于忍不住上前询问,语气带着一丝忐忑与探究。顾时安抬起头,眼神清明:“恰恰相反。
苏姑娘,你们家的松子枣泥酥,枣泥馅炒制时肯定用了陈年橘饼切极细的末,
而非普通糖渍橙皮,对吗?香气更内敛,回味有微酸,解腻增香,层次感极好。
”苏予甜吃了一惊:“您…您能吃出来?这是我曾祖母传下来的小诀窍,
现在很少有人知道了。”“还有这玉露霜,”顾时安指向另一盘白色云片糕状的糕点,
“炒米粉的火候极准,达到了‘熟化充分却无焦苦,
颗粒细腻仍保留微糙口感’的完美平衡点,米粉香和糖霜的甜融合得恰到好处。
这需要非常有经验的手感。”他的评价,精准、专业,直指工艺核心,绝非泛泛之谈。
苏予甜心中震动,对这个沉默寡言的男子刮目相看。“顾先生…您到底…”她忍不住想问。
“我研究风味。”顾时安简单回答,“传统点心是风味与时间的艺术。我想理解它,记录它,
或许…也能帮助它更好地延续下去。”他的话,触动了苏予甜内心最深处的渴望。
她一直梦想着能让沁芳斋的老手艺焕发新生,却苦于找不到方向和方法。眼前这个人,
似乎拥有她所欠缺的科学视角与理性分析能力。两人的交流由此增多。
顾时安不再仅仅是顾客,他开始更深入地观察沁芳斋的运作,并提出一些建设性的细节建议。
他看到苏予甜凭经验控制炒豆沙的火候,
会建议:“可以尝试用红外测温枪辅助判断糖浆的焦化点,更精准,稳定性更高。
”他发现店里包装仍用易渗油的油纸,
便提议:“可以考虑内部用糯米纸、外部用环保铝箔袋密封,既能保酥脆,又能延长保质期,
还更美观。”他甚至帮苏老先生调整了老面肥的养护环境恒温恒湿,
并用PH试纸监测其酸度变化,让发面效果更稳定。这些小小的改良,务实而有效,
潜移默化地提升着沁芳斋的出品稳定性和专业性,
也让苏老先生对这个“学院派”的年轻人渐渐改观。然而,
外部的压力并未因内部的微小优化而减轻。“酥礼坊”的金经理改变了策略,
从直接游说转为更隐蔽的渗透与挤压。首先,镇上开始流传关于沁芳斋的风言风语,
说其“手工制作卫生条件难以保证”、“用料来源不明”、“价格虚高性价比低”,
甚至暗示老人操作可能不符合现代食品规范。这些谣言恶毒而精准,
动摇了部分老街坊的信心。接着,
为沁芳斋供应了数十年顶级猪板油和当年新糯米的老供应商,
先后以“货源紧张”、“子女接手业务调整”为由,婉拒了后续合作。
苏予甜明显感觉到背后有一双无形的手在掐断他们的优质原料来源。最让她愤怒的是,
她无意中发现,“酥礼坊”竟然抢先一步,注册了“雪窗寒帖”的商标!
并将其作为一款“创新国风点心”进行了预告宣传,虽然产品完全不同,
但名字和概念无疑剽窃自顾时安带来的创意。“他们…他们怎么能这么无耻!
”苏予甜拿着手机上的预告页面,气得手指发抖。顾时安面色沉静,
眼中却闪过一丝冷光:“这是商业竞争中常见的恶意抢注。他们想用法律手段,
将未来的可能性扼杀在摇篮里。”“那我们…怎么办?”苏予甜感到一阵无力。“证据。
”顾时安冷静道,“我们需要证明,‘雪窗寒帖’这个名字并非他们首创,
且有历史渊源和我们在先的研究意图。你的曾祖辈可有留下任何笔记、配方残页?
哪怕只言片语也好。”苏予甜被点醒,立刻翻箱倒柜,
终于在祖父床底一个老旧的樟木箱深处,找到一本纸张泛黄脆弱的流水账本,
里面除了日常收支,竟真有寥寥数笔关于“仿古法制‘雪窗寒帖’,
用黑芝麻、松仁、微量陈皮入馅,形似墨锭,酥皮难成…”的记载,时间落款是七十年前!
“太好了!”顾时安仔细查看了账本,“虽然不够详细,
但足以证明这个名字和创意属于沁芳斋的历史尝试。我们可以以此为依据,
对他们的商标注册提出异议申请。”在他的指导下,苏予甜开始整理证据链,
撰写异议申请书。这个过程繁琐且专业,但顾时安的冷静与条理给了她巨大的支持。
共同应对外部压力的过程,极大地拉近了两人的距离。他们常常在打烊后,还留在店里,
对着电脑和古籍资料讨论至深夜。顾时安负责技术分析和法律条文梳理,
苏予甜则提供家族记忆和工艺细节。一个寒冷的夜晚,
两人又为查找一个关于古法用糖的记载忙到很晚。店里只剩他们两人,炉子上温着红枣茶,
香气袅袅。“谢谢你,顾先生。”苏予轻声道,递过一杯热茶,“没有你,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些…”“叫我时安就好。”顾时安接过茶杯,指尖不经意相触,
两人都微微一顿,“其实,应对商业竞争并非我的专长。我的专业是…让食物变得更好吃。
”他顿了顿,看向操作间里那些古老的工具:“但保护好这些能够产生真正美味的地方,
或许比研究本身更重要。”他的话,让苏予甜心中涌起一股暖流。
她看着他被灯光勾勒出的专注侧脸,忽然觉得这个原本疏离的男人,
身上有一种令人安心的沉稳力量。小寒节气,民间有食糯、熬糖的习俗。为应对原料危机,
也为了试验,苏予甜决定尝试用本地另一家小作坊产的新米糯米和土法红糖,
制作一批应节的红糖年糕。熬糖是关键。大铜锅里,红糖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
香气浓郁而焦香。苏予甜手持长柄铜勺,不断搅拌,观察着糖浆的浓稠度和颜色变化,
判断着最佳的出锅时机。“快到‘挂旗’了。”她有些紧张地自语,这是经验性的判断,
关乎年糕的甜度和口感。顾时安安静地站在一旁,
忽然递过来一个数字式糖度计:“试试这个。糖度达到78%左右,温度在115度时,
是风味和稠度的最佳平衡点,对应传统的‘小挂旗’状态。”苏予甜惊讶地接过,一试之下,
果然精准!新做的红糖年糕出炉后,甜而不腻,糯中带韧,带着浓郁的焦糖香气,非常成功。
“科技…有时候也能帮老手艺变得更准、更好。”苏予甜看着年糕,若有所思。
“工具是手的延伸,数据是经验的补充。”顾时安道,“尊重传统,不意味着排斥进步。
找到那个平衡点就好。”这次成功的尝试,像一道微光,照亮了迷雾中的前路。或许,
沁芳斋的未来,不在于固步自封,也不在于全盘商业化,而在于一种有根的创新。深夜,
顾时安告辞。苏予甜送他到门口。雪不知何时已停了,清冷的月光洒在青石板上,映着薄雪,
一片澄澈。“路上小心。”苏予甜轻声道。“嗯。”顾时安点点头,走了几步,又回头,
“关于‘雪窗寒帖’…虽然原始配方找不到,但根据记载的风味描述和工艺特点,
或许…我们可以尝试一起把它复现出来?”他的目光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清亮,
带着一种真诚的期待。苏予甜的心猛地一跳,随即涌起巨大的兴奋与勇气:“好!
我们一起试试!”小寒的夜,冷彻骨髓。但两颗因共同热爱而逐渐靠近的心,
却因一个全新的、充满挑战的目标,而变得火热起来。最冷的时节里,甜美的希望,
正在悄然孕育。第二章 完第三章 蜜渍金经理与“酥礼坊”的攻势,
如同小寒时节反复侵扰的湿冷寒气,无孔不入,试图从根基上瓦解“沁芳斋”的抵抗。
原料渠道的隐性封锁与商标抢注的恶意,让苏予甜倍感压力,
却也让她与顾时安之间的同盟关系愈发紧密。共同应对外部威胁的过程,像一道强韧的纽带,
将两人从最初的探询与好奇,迅速拉入一种休戚与共、并肩作战的深切状态。
“雪窗寒帖”的复现计划,成为了两人应对危机、寻找出路的核心焦点。
这不再仅仅是顾时安个人的学术兴趣,
更升华为一场为沁芳斋正名、捍卫其创新传承能力的实践。复现之路,艰难远超想象。
曾祖父的账本上只有“黑芝麻、松仁、微量陈皮入馅,形似墨锭,酥皮难成”这寥寥十余字,
最新章节
同类推荐
猜你喜欢
 方栀孟凌在恐怖游戏里当BOSS的枕边人全章节在线阅读_在恐怖游戏里当BOSS的枕边人全集免费在线阅读
方栀孟凌在恐怖游戏里当BOSS的枕边人全章节在线阅读_在恐怖游戏里当BOSS的枕边人全集免费在线阅读
玖日故事
 我家三口魂穿后,散装家庭开始合体了!(顾清竹顾回)热门网络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我家三口魂穿后,散装家庭开始合体了!顾清竹顾回
我家三口魂穿后,散装家庭开始合体了!(顾清竹顾回)热门网络小说推荐_最新完结小说推荐我家三口魂穿后,散装家庭开始合体了!顾清竹顾回
玖日故事
 《致命的真相》李小雅王亮免费完本小说在线阅读_《致命的真相》李小雅王亮免费小说
《致命的真相》李小雅王亮免费完本小说在线阅读_《致命的真相》李小雅王亮免费小说
佚名
 微醉野莓(玖日江希越)全本免费小说_阅读免费小说微醉野莓玖日江希越
微醉野莓(玖日江希越)全本免费小说_阅读免费小说微醉野莓玖日江希越
玖日故事
 发现室友的秘密系统后,我成了她的抽奖目标钱薇钱薇完本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免费阅读发现室友的秘密系统后,我成了她的抽奖目标(钱薇钱薇)
发现室友的秘密系统后,我成了她的抽奖目标钱薇钱薇完本小说大全_免费小说免费阅读发现室友的秘密系统后,我成了她的抽奖目标(钱薇钱薇)
玖日故事
 爱意未止,重逢正浓(周辞周谨之)完结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爱意未止,重逢正浓(周辞周谨之)
爱意未止,重逢正浓(周辞周谨之)完结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爱意未止,重逢正浓(周辞周谨之)
玖日故事
 男主黑化后,我又二次攻略(谢俞谢俞)完本小说大全_热门小说大全男主黑化后,我又二次攻略谢俞谢俞
男主黑化后,我又二次攻略(谢俞谢俞)完本小说大全_热门小说大全男主黑化后,我又二次攻略谢俞谢俞
玖日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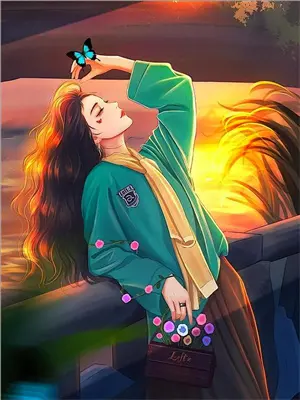 老公只给五百?这软饭谁爱喂谁喂(朵朵赵衍)在线免费小说_完结小说免费阅读老公只给五百?这软饭谁爱喂谁喂朵朵赵衍
老公只给五百?这软饭谁爱喂谁喂(朵朵赵衍)在线免费小说_完结小说免费阅读老公只给五百?这软饭谁爱喂谁喂朵朵赵衍
玖日故事
 江太太谁爱当谁当,我不伺候了洛薰江缊川免费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笔趣阁江太太谁爱当谁当,我不伺候了洛薰江缊川
江太太谁爱当谁当,我不伺候了洛薰江缊川免费小说推荐_免费小说笔趣阁江太太谁爱当谁当,我不伺候了洛薰江缊川
玖日故事
 摊牌了,我才是豪门亲生子(孟言澈苏以棠)好看的完结小说_完本小说摊牌了,我才是豪门亲生子孟言澈苏以棠
摊牌了,我才是豪门亲生子(孟言澈苏以棠)好看的完结小说_完本小说摊牌了,我才是豪门亲生子孟言澈苏以棠
玖日故事
 协议借种后,大伯哥他赖上我了(李景兰馥)免费阅读全文_免费完结版小说协议借种后,大伯哥他赖上我了李景兰馥
协议借种后,大伯哥他赖上我了(李景兰馥)免费阅读全文_免费完结版小说协议借种后,大伯哥他赖上我了李景兰馥
玖日故事
 出笼裴溯乔棉小说完整版免费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出笼(裴溯乔棉)
出笼裴溯乔棉小说完整版免费阅读_最新章节列表出笼(裴溯乔棉)
玖日故事
 顶级金丝雀的自我修养沈昭妍傅西辞小说完结推荐_热门小说阅读顶级金丝雀的自我修养沈昭妍傅西辞
顶级金丝雀的自我修养沈昭妍傅西辞小说完结推荐_热门小说阅读顶级金丝雀的自我修养沈昭妍傅西辞
玖日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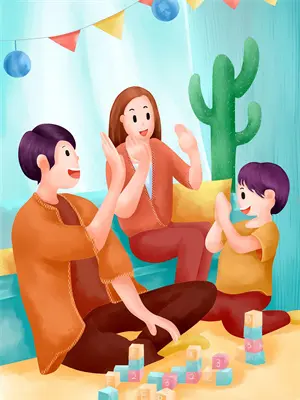 理念不合厨师娘拒绝预制菜人生(白芊芊姜子杰)免费阅读完整版小说_完结免费小说理念不合厨师娘拒绝预制菜人生(白芊芊姜子杰)
理念不合厨师娘拒绝预制菜人生(白芊芊姜子杰)免费阅读完整版小说_完结免费小说理念不合厨师娘拒绝预制菜人生(白芊芊姜子杰)
玖日故事
 魏湛魏湛毁我婚宴?那就用你的军功来赔!全章节在线阅读_毁我婚宴?那就用你的军功来赔!全集免费在线阅读
魏湛魏湛毁我婚宴?那就用你的军功来赔!全章节在线阅读_毁我婚宴?那就用你的军功来赔!全集免费在线阅读
玖日故事
 玖日傅斯年眼看老板气运归零全文免费阅读_玖日傅斯年完整版免费阅读
玖日傅斯年眼看老板气运归零全文免费阅读_玖日傅斯年完整版免费阅读
玖日故事
 穿成恶毒女配,在男女主宿舍当卧底(乔子尧洛欣怡)免费阅读全文_免费完结版小说穿成恶毒女配,在男女主宿舍当卧底乔子尧洛欣怡
穿成恶毒女配,在男女主宿舍当卧底(乔子尧洛欣怡)免费阅读全文_免费完结版小说穿成恶毒女配,在男女主宿舍当卧底乔子尧洛欣怡
玖日故事
 闺蜜重生团目标,灭渣男,当富婆!唯意商玦小说完整版_热门好看小说闺蜜重生团目标,灭渣男,当富婆!(唯意商玦)
闺蜜重生团目标,灭渣男,当富婆!唯意商玦小说完整版_热门好看小说闺蜜重生团目标,灭渣男,当富婆!(唯意商玦)
玖日故事
 爱他,不过尔尔(莫莉霍瑾年)热门小说_《爱他,不过尔尔》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爱他,不过尔尔(莫莉霍瑾年)热门小说_《爱他,不过尔尔》最新章节在线阅读
玖日故事
 傅明轩傅行知(妈妈,为什么爱的不是我)全章节在线阅读_(妈妈,为什么爱的不是我)完结版免费阅读
傅明轩傅行知(妈妈,为什么爱的不是我)全章节在线阅读_(妈妈,为什么爱的不是我)完结版免费阅读
玖日故事







